当提及杨振宁这个名字,许多人的脑海中会立刻浮现出诺贝尔奖的光环以及那些深奥的物理公式所代表的科学高度。然而,对于电子科技大学粒子物理与核物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及博士生导师王志伟来说,杨振宁先生的影响却深深镌刻在更为具体而珍贵的时光之中。
2008年,还在上海读大学的王志伟有幸聆听了年近九旬的杨振宁先生全程脱稿、语速轻快的中文讲座。这场讲座不仅让他在学术上收获颇丰,更在人生的选择上给予了他深刻的启示。在近二十年的科研道路上,王志伟始终带着这份来自杨振宁先生的影响前行,这份传承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学术指引,成为了一份指引年轻研究者如何选择方向、如何做学问、如何坚守初心的宝贵精神坐标。
当听到杨振宁先生逝世的消息时,37岁的王志伟感慨道:“这并不像是一个遥远的名人离开了我们,更像是一位熟悉的长辈离我们而去。”在他看来,缅怀杨振宁先生的最佳方式,就是深入阅读他的学术人生。他特别提到了那两本被自己“翻烂”的《曙光集》和《晨曦集》,这两本书成为了他理解杨振宁学术思想的重要窗口。

杨振宁 图片来源:央视视频截图
NBD:您的研究领域是基于“杨-米尔斯理论”在暗物质领域的探索,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从这个角度切入?
王志伟:2008年前后,我还在上海读大学本科。当时杨先生来复旦大学做讲座,我怀着追星的心情,现场聆听了这场讲座。尽管已近九旬高龄,但杨先生的精神状态极佳,全程用中文演讲,思路清晰,语速快捷,几乎完全脱稿。演讲时虽然播放了PPT,但他常常只是扫一眼,基本不用看。
在那场讲座中,杨先生特别强调了年轻人的学术研究“品位”。他对理论品位的理解,并非仅仅基于一个理论能够实现什么,而是这个理论是否足够简洁、漂亮,同时又非常丰富。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我在丹麦做博士后时,与我的合作导师——一位丹麦的院士——一致认为,首选“杨-米尔斯理论”来切入暗物质的理论研究。尽管物理学的理论模型众多,但千挑万选后,我们认为最简洁且足够丰富的理论框架就是“杨-米尔斯理论”。
NBD:杨振宁先生的那堂讲座,对您后续的道路还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志伟:那场讲座不仅对我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影响,更对我后续的人生方向产生了触动。除了“学术品位”外,杨先生回忆自己的人生选择也让我印象深刻。
早年,他出国留学时瞄准的是实验物理学方向,但很快发现自己并不擅长这方面。他意识到自己在理论物理学方面更有天赋,于是果断放弃了实验物理学,转向了理论物理学。这种果断的选择对于一般学生来说很难做到,他们可能会因为已经付出了两年时间而选择先毕业或如何。但杨先生却直接转到了理论物理学领域。这让我意识到,学术领域有一个频谱,你需要去感受哪一个谱段、哪个区间最适合自己。因此,在后面我也做出了自己研究区间段的选择,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初杨先生讲座的影响。
2010年我出国留学,2022年回来。中间的12年里,我其实没有与杨振宁先生有直接接触。但他做的公开学术报告上网后,我都会去认真学习。同时,我也买了他的各类书籍和传记,好好去揣摩他的想法。《曙光集》和《晨曦集》都被我翻烂了。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写到邓稼先先生时,笔尖流露出的感情是一个科学家对祖国深深的情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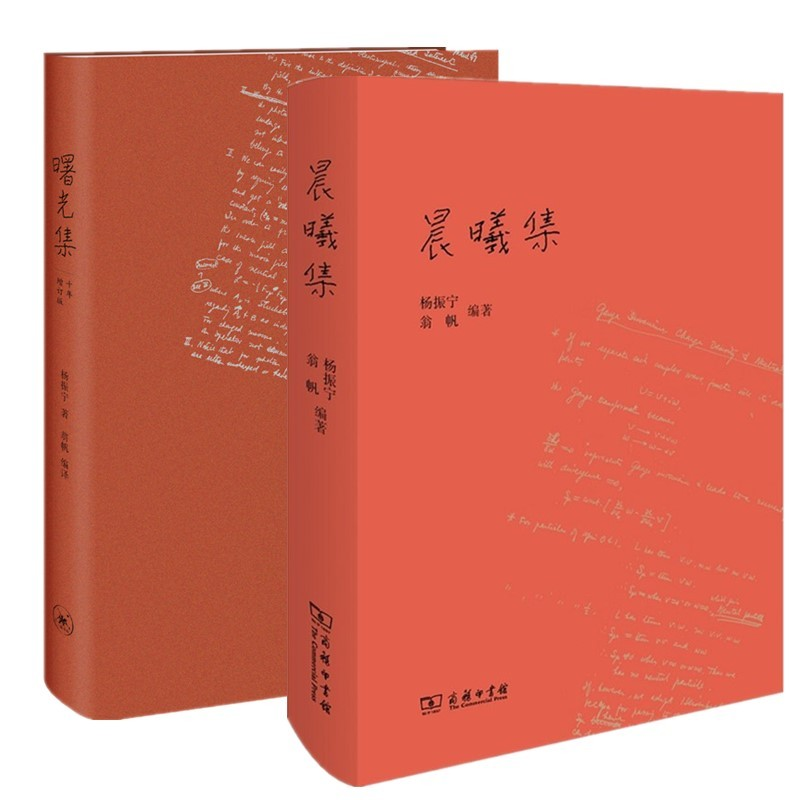
《曙光集》《晨曦集》 图片来源:购物平台截图
NBD:作为普通大众,应该怎样理解“杨-米尔斯理论”对于科学界的贡献?
王志伟:杨先生有很多杰出的科研成果,但其中有两项最为重要。第一项是他与米尔斯一起创立的“杨-米尔斯”规范场。用今天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杨先生的一句话:“对称性,决定相互作用。”第二项是他与李政道先生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
“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使我们对自然界中的“力”及其相互作用的机制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它也是构成粒子物理领域“标准模型”的奠基石。而粒子领域的“标准模型”类似于化学当中的元素周期表,它是对现有已知粒子以及粒子与粒子之间相互作用进行系统分类的理论框架。打个比方,在盖房子前,它既帮我们弄清有哪些“砖块”(基本粒子),又指明了把砖块黏在一起的“水泥”(相互作用)是什么,而且还告诉我们它们如何按规律组合。
基于标准模型的各种实验检验,又催生并迭代了很多代粒子“加速器”。这些加速器进一步催生了很多新的技术,比如超导材料,在医疗(如核磁共振、质子治疗)、电力、交通(超导磁悬浮)等领域有广泛运用。
其实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很多来源于数十年前的基础理论探索,只是在转化链条与产业化中滞后显现。最有名的实际上是万维网,它最早建立在欧洲的核子中心,是为他们内部的资料共享而设计的,后来演变成我们今天在互联网上浏览网页、点击链接的通用方式。
前沿的理论物理研究就是如此,有时候你并不是完全为了某项应用技术而研究,但最后其实带动了很多技术的发展。
NBD:现在您基于“杨-米尔斯理论”探究暗物质的最新进展是什么?
王志伟:前面我们说了“杨-米尔斯理论”为理解物质世界的基本构成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宇宙中充满了人们看不见的“暗物质”,我们假设在看不见的暗物质的世界里,同样也由“杨-米尔斯理论”所描述。在早期工作中,我们借此来提取早期宇宙的引力波信号。后面我们基于“杨-米尔斯理论”,提出暗物质的构成可以是“胶球”,这是强相互作用、凝结成团的复合型粒子。
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的刘江来教授对我们的理论特别感兴趣,他主持了panda-X暗物质探测实验,并希望能基于“胶球暗物质理论模型”在panda-X上进行探测验证。
NBD:您觉得杨振宁先生回国对中国科研领域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王志伟:杨先生这个人很真,我看过他回国后的很多学术报告实录。报告一开始,他就坦言自己已不在科研一线,他不去立什么“诺奖获得者90多岁还在科研一线”的人设。一个归国的大科学家,在公开场合直接讲他已经不在科研一线,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我觉得比起直接可见的科研成果,杨先生回国对中国物理学界的意义在更深远的层次上。杨先生作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他的回归带来了顶尖的学术交流。同杨振宁先生一起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姚期智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曾透露,当年毅然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职,是应来自杨振宁的回国邀请。作为杨振宁的弟子,斯坦福大学物理系教授张首晟担任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的特聘教授,每年回国数月授课。
杨先生多次面向青年学子做学术报告、公开演讲,给到包括我在内的青年人实实在在的精神引领。还有,他投身一线教学。此前似乎有一种风气,资深的大牌教授不太愿意给本科生上基础课。但杨先生回到清华后,身体力行亲自备课,给物理本科生讲授大学一年级的基础课。他这么做了,也会带动别人这么做。所以他对青年学子的影响,可谓代代传承。

杨振宁先生为清华大学本科生授课 图片来源:央视视频截图
NBD:杨振宁先生不仅在物理、数学这些理科类有极高的造诣,他的人文修养其实也很强。您怎么看人文修养对学术品位的影响?
王志伟:不仅仅是杨振宁先生,比如李政道先生作画、写诗都很棒,还有数学家丘成桐先生、物理学家丁肇中先生等。他们这批科学家纠正了我以前的一个误区。我以前其实是比较偏科的,对于人文类东西的兴趣完全不如对纯自然界的追求。但是慢慢地,我也意识到人文修养的重要性。我现在也慢慢对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产生研究兴趣,也会花时间去专门学习。有时候理科的灵感来源,就来自这种跨学科的研究。
NBD:您怎么看杨振宁先生为中国学界留下的精神遗产?
王志伟:有一点特别值得一提,如果没有杨先生和李先生,我们在做一些极富挑战性的理论物理科研课题时,可能会想中国人是否够聪明。因为感觉在现代物理学界,之前所有的重要成果都是外国人做出来的,好像中国人无法胜任理论物理的杰出工作。但杨先生和李先生的出现给了大家信心,中国人是可以的。这让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敢于去挑战重要的科学课题,因为只有我们不自卑,才敢于去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