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的北京大学课堂上,胡适手持《尚书》猛拍讲台的场景成为史学界标志性画面。当他说出'《夏书》里的夏朝全是后世添上去的'时,台下学生哗然,有人当场反驳:'司马迁《史记》都写了,怎么会是假的?'这场争论背后,是中国史学界'信古'与'疑古'思潮的激烈碰撞,而胡适提出的验证方法,恰似一把钥匙,开启了破解夏朝之谜的百年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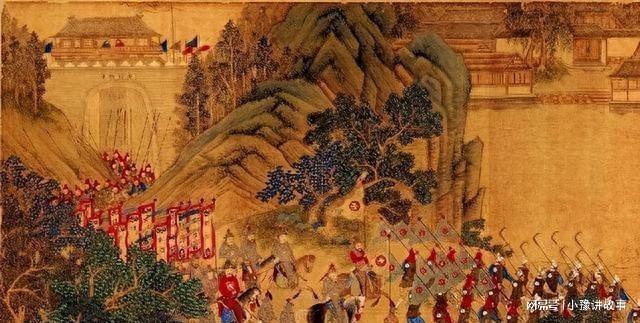
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胡适将古史体系拦腰斩断,从老子、孔子讲起却对夏朝只字不提。当被问及是否否认夏朝存在时,他明确回应:'不是不承认,是没证据不敢认。'这种态度源于清末民初西方实证史学的传入,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理论指出,越晚的史书对古史的记载越详细,夏朝故事可能是后人编造的。
当时没有任何实物能证明夏朝存在,《史记·夏本纪》中大禹治水、启建夏朝的记载全无出土文物对应。受杜威实用主义影响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史学的灵魂是证据,没有证据,再好的故事也是神话。'这种严谨态度在1899年甲骨文发现后得到强化,当殷墟遗址出土文物与《殷本纪》记载完全吻合时,胡适在1922年《努力周报》上明确提出:'证明夏朝存在,就照商朝的办法来——找地下的实物与纸上文献相互印证。'
1899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因疟疾发现'龙骨'上的刻痕,这个偶然发现开启了商朝验证的序幕。1903年刘鹗出版《铁云藏龟》首次公开甲骨文,但直到1917年王国维对照甲骨文与《殷本纪》,发现商王名号完全吻合。1928年殷墟遗址的发掘更是出土了记载战争、祭祀细节的甲骨文,与文献形成完美闭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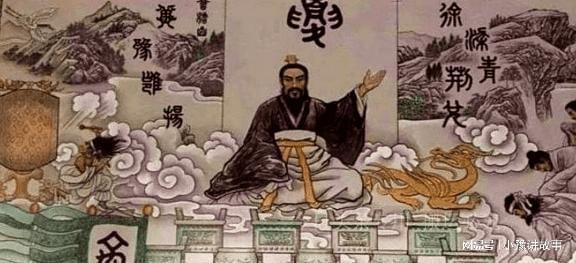
商朝的'复活'给胡适带来深刻启发,他在日记中感叹:'商朝能这么证,夏朝为什么不能?'但夏朝比商朝早千年,寻找证据的难度呈指数级增长。1931年徐旭生向胡适请教寻找夏朝实物的方法时,得到的指引是:根据《史记》记载,应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寻找,但具体位置需要考古发掘确定。
寻找夏朝遗址面临两大难题:时间定位与器物辨识。商朝有甲骨文定年,夏朝却连文字都没发现;商朝青铜器特征明显,夏朝器物样式未知。1936年徐旭生带队考察豫西,沿伊河、洛河走访三个月,仅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抗战爆发后,考古工作中断,胡适安慰徐旭生:'考古是慢功夫,我们这代找不到,下一代总会找到。'
这个等待持续了二十三年。1959年71岁的徐旭生再次带队,在偃师二里头村发现了300万平方米的大型遗址。出土的宫殿基址、青铜礼器、铸铜作坊经碳十四测年,显示距今3800—3500年,正好对应夏朝晚期。特别是比商朝早几百年的青铜爵,被夏鼐认定为'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
尽管二里头遗址的年代与夏朝晚期吻合,但出土陶器上只有刻画符号而无成熟文字,这成为争议焦点。有人质疑这是商朝早期遗址,支持者则指出其年代早于郑州商朝早期遗址。这场争论再次回到胡适的方法论——缺乏文字证据,就无法100%确定是夏朝。
胡适生前多次强调验证需要耐心。1930年他在演讲中说:'考古要慢慢来,不能为了凑五千年文明就造假。'这种严谨态度影响了后世考古学家。二里头遗址发掘60多年来,考古队始终未急于宣称'这就是夏都',而是持续积累证据。

2002年二里头出土的70厘米绿松石龙形器,由2000多片绿松石拼成,被考古学家认定为夏朝'国之重器'。2019年发现的大型绿松石镶嵌铜牌饰,在商朝遗址中也有发现,证明文化传承关系。都城布局方面,二里头宫殿居中,周围分布手工业作坊和居民区,这种功能分区与商朝殷墟高度相似,显示其作为成熟王朝都城的特征。
这些证据虽未发现文字,但与文献记载的'夏朝特征'高度吻合。'考古中国'项目2023年报告指出:'二里头遗址为研究夏朝历史提供了关键实物证据。'但学术界仍存在争议,支持者认为商朝早期也未发现多少文字,不应将文字作为唯一标准。
胡适提出的验证方法,彻底改变了中国史学研究范式。在他之前,古史研究全靠文献;在他之后,考古成为核心手段。顾颉刚回忆:'胡适先生的'找证据',让我们从书斋里走了出来,去地下找答案。'这种转变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达到新高度,通过碳十四测年、器物比对,将夏朝年代定在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

2024年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开馆时,展出的绿松石龙形器前总围着游客。当被问及'这真的是夏朝的东西吗?',讲解员会笑着说:'这是离夏朝最近的证据。'或许,能否100%确定夏朝存在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胡适的方法教会我们:用实证态度对待历史,不盲从、不臆断,这才是探索文明真相的正确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