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纳森·罗森鲍姆
译者:易二三
校对:覃天
来源:The Guardian(2002年9月21日)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在1970年至1982年间拍摄的八部短片,堪称检验影评人对世界电影认知深度的试金石。这些作品虽在诞生地伊朗未激起广泛讨论,却因导演后续创作的长片杰作逐渐获得国际关注,最终成为电影史上不可忽视的独特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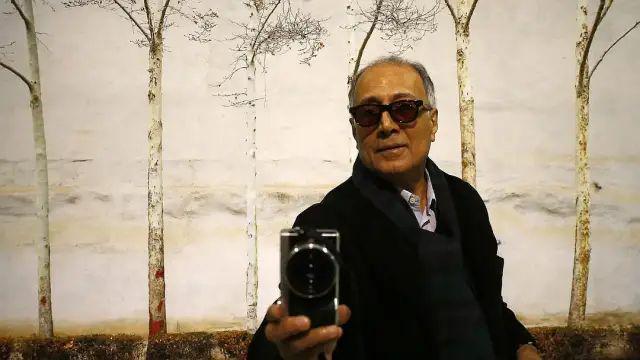
这种现象印证了一个残酷现实:所谓“世界电影”的认知往往被商业宣传所绑架。当我们将视野局限于被大肆炒作的影片时,实际上是在接受制片人、策展人、发行商乃至影评人构建的筛选机制——而这些机制筛选出的作品,多数经不起艺术价值的推敲。
阿巴斯的创作轨迹颇具启示性。这位60年代以商业艺术家身份起家的导演,从海报设计转向电视广告后,于1969年受邀加入伊朗儿童和青年智力发展研究所(Kanun)。这个国家机构资助的创作环境,催生了其早期兼具实验性与娱乐性的教育电影。尽管阿巴斯自称拍摄时未以艺术家自居,但这些作品却意外推动了伊朗儿童电影的时尚潮流。

教育片外壳下的哲学实验
为Kanun创作的最后两部作品《特写》(1990)和《生生长流》(1992),已显露出阿巴斯成熟的叙事风格。而早期短片如《课间休息》(1972)、《一个问题的两种解决方法》(1975)等,虽多以学校为场景,却通过布莱希特式的教育剧形式,探讨着协作与冲突、秩序与混乱等永恒命题。
这些作品展现出惊人的形式创新:
- 《我也能》(1975)用动画片段解构儿童模仿行为
- 《有序或无序》(1981)通过对比学生与成人行为,质疑社会规则的合理性
- 《合唱团》(1982)以老人关闭助听器的动作,探讨声音与沉默的哲学

长片中的短片基因
阿巴斯后期长片中反复出现的核心元素,早在这些短片中就已埋下伏笔:
-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1987)的蜿蜒山路与《面包与小巷》(1970)的街道构成空间呼应
- 《橄榄树下的情人》(1994)对非专业演员的重拍机制,延续了《一个问题的两种解决方法》的叙事策略
- 《随风而逝》(1999)中记者反复接听手机的动作,与《有序或无序》的重复结构形成互文

问题导向的影像哲学
阿巴斯属于那种将镜头视为提问工具的导演群体,这个阵营还包括约翰·卡萨维蒂、克里斯·马克、塔可夫斯基等人。他们拒绝提供传统叙事答案,转而用长镜头构建哲学命题。这种创作方式虽常令观众困惑,却开辟了电影表达的新维度。
最具颠覆性的是《十段生命的律动》(2002),这部作品彻底消解了导演的干预痕迹。阿巴斯将自己比作足球教练,仅在场景切换时按铃,这种“去作者化”的尝试,与其早期短片中刻意暴露创作过程的做法形成有趣对照。

被忽视的电影版图
当阿巴斯创作这些短片时,西方影评界正热衷于构建“中心-边缘”的世界电影格局。美国、欧洲、日本被视为核心产区,而印度、非洲、伊朗等地的电影仅被视为地方性表达。这种认知偏见导致无数优秀作品被埋没,阿巴斯的早期创作正是这种筛选机制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幸存者。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我们似乎重蹈覆辙:当更多电影争夺注意力时,真正的艺术发现反而变得更加困难。阿巴斯的短片提醒我们,世界电影的丰富性永远超出主流视野的边界,而发现这些被遗忘的珍宝,需要影评人具备打破认知框架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