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Victoria Loy
译者:Issac
校对:易二三
来源:《Senses of Cinema》
(2005年4月)
在路易斯·布努埃尔的电影宇宙中,《女仆日记》(1964)被评论家索尔·奥斯特里茨归类为导演「优雅讽刺的欧洲阶段」代表作,与《泯灭天使》(1962)、《白日美人》(1967)、《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1972)共同构成其创作巅峰期的核心文本。这部改编自奥克塔夫·米尔博小说的作品,通过黑白影像与精妙叙事,将超现实主义美学与阶级批判熔铸成一部充满隐喻的黑色寓言。

相较于布努埃尔其他超现实主义作品,《女仆日记》呈现出罕见的叙事克制。影片摒弃了非线性联想与梦境符号,转而以线性叙事包裹超现实内核——性与死亡的并置、社会秩序与情欲吸引的冲突,构成贯穿全片的主题矩阵。这种「隐形的超现实」通过场景调度悄然渗透:当蒙蒂尔夫人与神父讨论亲密关系时,侍女塞莱斯汀的突然闯入,恰似《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中社交宴会被死亡打断的先声。
导演采用法式宽银幕镜头(Franscope)构建视觉空间,蒙蒂尔庄园的室内布景堪称阶级符号的陈列馆:半身像、古董花瓶与镀金灯具交织成物质文明的牢笼。当夫人用「哪些物品必须保存」的训诫确立等级秩序时,镜头以俯拍视角强化了这种权力关系的荒诞性。这种视觉策略与让·雷诺阿1946年版本形成微妙互文,尽管布努埃尔否认受其影响,但两者对法西斯美学的警惕不谋而合。

侍女塞莱斯汀是布努埃尔塑造的矛盾综合体:她蔑视资产阶级的虚伪,却精心模仿他们的穿着;她拒绝爱情至上,却选择与上尉结合。这种行为逻辑的断裂,恰是导演对无意识驱动的诠释。相较于米尔博原著中与猎场看守人约瑟夫的恶魔式纠缠,布努埃尔赋予她更自由的道德选择——当她穿着白色斗篷调查约瑟夫时,制服既是护身符也是诱惑工具,暗示着权力关系的可逆性。
影片对「黑色皮靴」的反复呈现堪称神来之笔。这双象征法西斯美学的物件,在塞莱斯汀脚上是阶级身份的标识,在游行队伍中则化为暴力机器的隐喻。当约瑟夫擦拭靴子的特写与教堂司事助手同框时,布努埃尔完成了对教会与极权主义合谋的尖锐批判。这种符号学运用,使影片超越阶级叙事,直指20世纪30年代法国法西斯崛起的政治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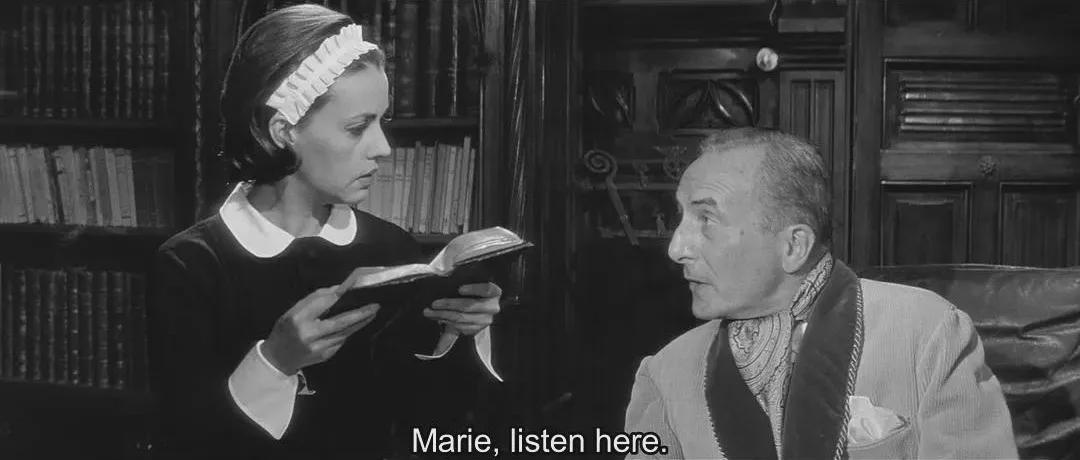
布努埃尔的镜头语言始终服务于主题表达。在瑟堡示威场景中,约瑟夫高呼「基亚佩万岁」的台词,既是对审查制度的嘲讽(布努埃尔1930年《黄金时代》遭禁映),也是对法西斯美学的解构。这种将政治笑话嵌入叙事肌理的手法,使影片在娱乐性外获得更深的批判维度。正如联合编剧让-克劳德·卡里埃尔所言:「神秘不应来自光影技巧,而应诞生于门的吱嘎声与慢镜头之中。」
影片结尾的秋日庄园长镜头,将超现实主义的荒诞感推向极致。灰暗色调中,塞莱斯汀的白色身影逐渐消失,暗示着非理性力量对理性秩序的悄然渗透。这种视觉留白,恰是布努埃尔对资产阶级社会终将崩塌的预言式书写。

作为布努埃尔创作生涯中被低估的杰作,《女仆日记》以其精妙的叙事控制与政治隐喻,构建了一个关于阶级、宗教与权力的超现实迷宫。当观众细品影片中那些看似荒诞的细节时,终将发现:每个笑话背后,都藏着对人性弱点的致命一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