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韩剧《暴风圈》因角色设定引发广泛争议,剧中一位接受美式教育的间谍之女与一位身世成谜的朝鲜“兵王”,竟对韩国表现出绝对忠诚。这种矛盾设定不仅让观众感到困惑,更折射出韩国影视创作中深层的文化困境。《侃点影》主持人施佬与冬晓通过剖析该剧人物塑造,揭示其背后“恨文化”的民族心理,探讨韩国在构建民族叙事过程中的挣扎与错位。
冬晓:《暴风圈》中女主角的设定堪称离奇。她父亲是韩国政府认定的间谍,被捕后坚贞不屈,最终英勇就义。母亲为躲避迫害,带着她远渡重洋赴美,靠做美甲供她读书。然而,编剧却让这样一个背负杀父之仇、长在星条旗下的角色,对韩国表现出无比热爱与忠诚。更荒诞的是,女主婆婆竟以“比土生土长的韩国人更爱国”为由,接受她成为儿媳,认为这有助于儿子竞选总统。
施洋:男主角的设定同样令人费解。他是一位能力超群的“兵王”,国籍未知,疑似朝鲜脱北者,曾辗转蒙古、伊拉克、越南等地,加入雇佣兵组织瓦尔基里。剧中不断强调他是自愿保护女主角,尽管起初极不情愿。他的能力远超原有安保团队,嘴上说是为维护半岛和平,实则将朝鲜部分完全忽略,从爱女主上升到爱韩国。两人拥吻时,借由女主的性魅力,民主的韩国似乎实现了对朝鲜的“驯化”与“征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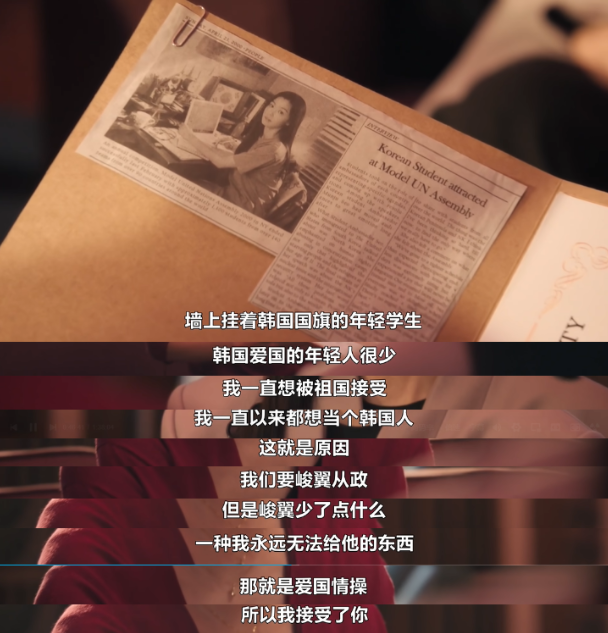
冬晓:这让人联想到另一部南北分断电影《铁雨》。虽然从中国人视角看,其剧情有些脱离现实,但对朝韩主人公的刻画远比《暴风圈》高明。一个是朝鲜兵王,一个是韩国情报头子,两人意识形态坚定,却因对和平的共同追求而并肩作战,最终各执己见又通力合作。这反映出当时韩国影视从业者愿意平视朝鲜,将其视为平等的对手甚至可能的合作伙伴。
而《暴风圈》中,男主作为朝鲜脱北者,身上却完全看不到“朝鲜”痕迹,国籍未知更像是一种“没有归属感”的含蓄表述。既然没有归属感,又何必压上身家性命保护韩国政治遗孀?这种模糊处理背后,隐藏的是韩国人对自己身份的错乱认知。
施洋:将几部同类型影片横向比较,会发现这类南北分断片中朝韩人设的改变,反映了近几年韩国思潮的变迁。早年韩国特工片中,朝鲜特工形象更高大,甚至能舍弃前途保护韩国特工,流露出一丝对朝鲜的认可。而《爱的迫降》和《暴风圈》则走向另一个极端,朝鲜角色遇到韩国女性便立刻爱得死去活来,没有任何情感或道德挣扎,直接“恋爱脑”上头。
冬晓:这种表现手法过于低级。若想证明韩国女性的优越,应采用更精致的手法。比如,在讲述英雄冒险故事时,反派塑造得越强大,英雄战胜反派时的形象就越伟岸。只有着重表达脱北者在背叛母国投奔韩国时的内心对抗,才能更突出韩国在国家制度建设上的正确性。
施洋:男女主身上的身份“buff”更像是制服上的标签,典型的工业流水线产物。大女主应该在美国读书、说流利英语、嫁入豪门……把这些标签挂上,主角就塑造得差不多了。男主同理,要形象好、在朝韩间游移、脱北后要有家人留在北方且是好人……如此往上套,最后就像朝鲜人民军将领一样,身上一排排勋章。
冬晓:《暴风圈》上映后,不仅被中国网友吐槽,也遭到伊拉克和越南网友批评。剧中男主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战,将两国遭遇的战争痛苦简化为吹嘘男主军事能力的台词,显得非常不严肃。更别提2000年后越南几乎没打过仗,这种设定在严肃电视剧中显得过于轻佻。
那么,韩国文艺作品为何会呈现这种奇怪的创作倾向?只能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暴风圈》的离谱设定,是韩国人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呈现。
施洋:剧中不断强调两个主角对韩国的爱,而他们都不是土生土长的韩国人。这无意中表露了一个现实:韩国本土政客身上不存在对韩国的赤诚之爱,因为对内求而不得,所以必须寄希望于向外找寻,通过强调外来者的忠诚来表达对自我的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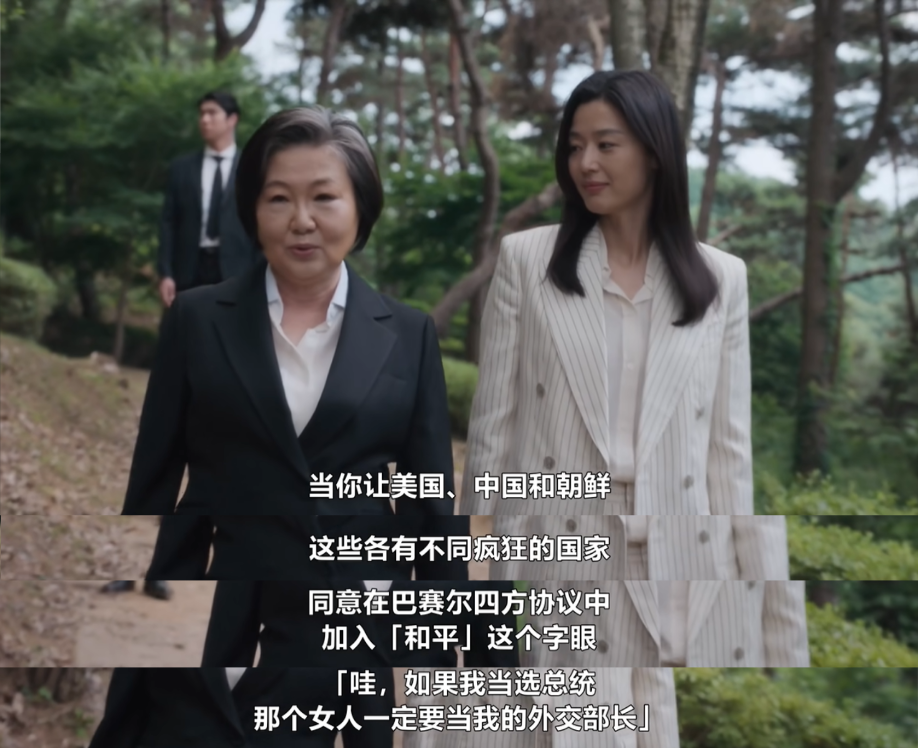
冬晓:类似的自恋情结在《暴风圈》中比比皆是。比如,韩国总统夸女主业务能力强,凭一己之力让中、美、朝三国在某个协议中加入和平字眼,这与现实中《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上只有中、美、朝三国代表签字、韩国连桌都上不去的境况形成鲜明对照。战场上拿不回的领土,谈判上也不可能拿回来;战场上得不到的尊重,荧幕上也变不出来。
韩国影视作品中对国际政治的表达总给人别扭之感。关于这点,韩国人提出过一个概念叫“恨文化”,认为这是韩民族强烈的心理文化,是对历史上无法自控的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的一种悲愤回应。这种集体痛苦经历在历史演变中被铸造成一种共同的集体无意识,在南北分断片中体现得最为准确。
“恨文化”由韩国人自己提出并再三强调,不同于日本人对《菊与刀》中“耻文化”的模糊态度。从个人层面看,它是对历史浪潮身不由己的怒火;从国家层面来说,则是对韩国所处地理之复杂、多年来被邻国欺压无力反抗的愤懑。
长久压抑愤怒的结果是必须寻找发泄口。按照正常逻辑,被欺负了就要报复,所以报复主题的影视作品在韩国特别流行,如《黑暗荣耀》《妻子的诱惑》《金福南杀人事件始末》《老男孩》等。但韩国的特殊之处在于,究竟该将报复的矛头对准谁,始终语焉不详。
韩国人在谈及“恨文化”时多半会声明,这种恨是没有针对性的,是自发的,是对自己没有能力改变悲惨现状的恨。但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上,会发现这只是一种自我开脱的说辞。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韩国人对于过去不能针对性的恨,其实映射的是对今天不能针对性的恨。
有怨报怨,有仇报仇。日本殖民朝鲜,那就该恨日本;可放眼韩国大财团,有哪个和日殖时期的伪政府没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不敢恨。朝鲜停战,美国人在这里驻军,默许军事独裁者统治韩国,同时在经济和文化上不断破坏韩国的自主性,这不该恨吗?是的,这不敢恨,毕竟美国人不点头,民选的韩国总统也坐不进青瓦台。因此,韩国人以无针对性的恨对自己的懦弱开脱,进而放纵这种恨外溢,对准中国,也就不奇怪了。
施洋:真恨的话,那韩国的左翼叙事就越界了。日殖遗毒把握着韩国的经济命脉,美国则多管齐下,对韩国的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不断侵蚀。一旦承认了这些,韩国还怎么标榜自己是民主国家?哪有民主国家还没结束殖民的。
韩国的文艺作品里,一方面充满了左翼思潮,因为影视圈里左翼人还挺多,比如368这一代;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保持着小心翼翼,知道能说到哪,再多说两句就不行。比如奉俊昊的《汉江怪物》,里面就隐晦地点了一下驻韩美军,但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说。
冬晓:大部分遭受过长期殖民的国家,在解除殖民状态后,都要面对如何重建民族叙事的问题。对于通过不断斗争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而言,这不难。哪怕斗争比较弱,只要在谋求民族解放的过程中有这么一支力量存在,那独立后民族内核都会很稳定,胜利的叙事会顺理成章地取代苦难的叙事,从受害者的身份里挣脱出来,蜕变为自我命运的掌控者。
比如印度,在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指导下,从英国殖民者手中获得独立的过程远不如阿尔及利亚从法国殖民者手中获得独立的过程艰难、血腥,而且还有印巴分治的历史遗留问题。但印度给人印象就是超出常人可以理解的自信,以至于印度也喜欢拍复仇类型的影片。可印度拍出的复仇片,就没有韩国拍的那么压抑内耗,甚至(当然这里有部分宗教因素)印度的复仇片认可复仇的合理性却同时批判被怒火蒙蔽心智的人得不到真正的救赎,这就是《因果报应》结局中女孩要对施暴者说“我饶恕你”的深层原因。

施洋:韩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确实与李承晚时期的历史遗留有关。本来在李承晚之前,韩国一度还有成为正常国家的操作空间。大韩民国在上海有临时政府,在重庆也有临时政府,如果能以这些为基础去建设二战后的韩国意识形态,虽然也会有一些软弱性和糟粕,但也能勉强行得通。
然后,金九就被杀了,接着从美国搞了一个人来治理韩国,问题就越来越多。初代韩国的民主人士在争取韩国独立和自由上做出了很多贡献,结果现在的韩国和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在这个过程中,一切变得越来越糟。先是李承晚带来的这帮腐朽的美国洋买办,后面维新政府朴正熙上台,清除了这帮坏人,却又开始搞军事独裁。军事独裁到了后期开始明目张胆地反民主。最让人郁闷的是,韩国摆脱殖民统治后的第一代政权,竟然是一帮日伪分子的残余建立的。
慢慢的,韩国经济进入了成长期,这里面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处于所谓非民主化的军事独裁军政府时期,这就进一步加深了韩国民族自主叙事的障碍。
金泳三的文人治国听着光鲜,大家以为现在好起来了,但实际上如果美国没有赏的那仨瓜俩枣,韩国90年代的飞黄腾达,自己能够实现多少?它的经济腾飞,前一半要归功于冷战时期的美国产业分工,后一半要归功于冷战结束后的美国产业再分工。
冬晓:韩国人努力地给自己的民族性找了一个恨文化的解释,实际上却根本圆不回来。自己没有在抗争中胜利过,所以体会不到胜利的滋味,也无法理解强者的心理。这让我想起之前看韩国人写自己恨文化的著作时,引用过法国历史学家勒南的一句话,说悲愤比胜利更有价值。怎么说呢,人家法国人好歹有个拿破仑曾经大赢特赢过,搞得欧洲瑟瑟发抖,二战勉强算是战胜国。韩国以此作为韩民族文化心理的注脚,多少就有些不太应景了。
因为自己习惯了阴暗爬行,所以便觉得大家都在阴暗爬行,自己是什么样的人,那看别人就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从我个人的观感来说,《暴风圈》与其说是在辱华,倒不如说是韩国人在辱自己,而中文互联网的反应,更多也是对厌蠢症的生理性厌恶。中国人现在足够自信,其实并不介意在外国人拍摄的影视作品中成为反派,比如《太空部队》《铁雨》。未来随着真正整理过历史动荡的那一代的影人(368)逐渐退出,从小听着韩国民主神话成长的这一代制作人掌权,类似的降智作品还会越来越多。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