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彭,立刻来北京,越快越好!”1950年9月16日凌晨两点,电话里林彪的嗓音显得有些沙哑,却透出少见的急切。彭富九在武汉放下话筒,心中已经明白:仁川登陆带来的风暴,比所有人想的都猛。

回到前一天——9月15日,美第10军在仁川强行登陆,半岛局势突然翻面,原本胶着的前线被撕开缺口。其实中央早在七月就给平壤捎过信:“小心美军从西海岸抄后路。”只是斯大林没松口,中国出兵的设想停在纸上。眼看人民军主力被牵制在洛东江,后背又被敌军割裂,毛主席那句“九月底前准备完毕”立刻显得分外刺耳——准备归准备,真要谁领兵冲过去?
当时总参内部传着一份“能打立体战的六人”名单: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粟裕、陈赓。刘伯承忙着筹建陆军大学;徐向前旧伤复发,连总参的公文都由聂荣臻代签;陈赓已经套好草帽去了越南;粟裕高血压加美尼尔氏综合征,在苏联医院打点滴。纯粹算下来,只剩彭、林二人“健康在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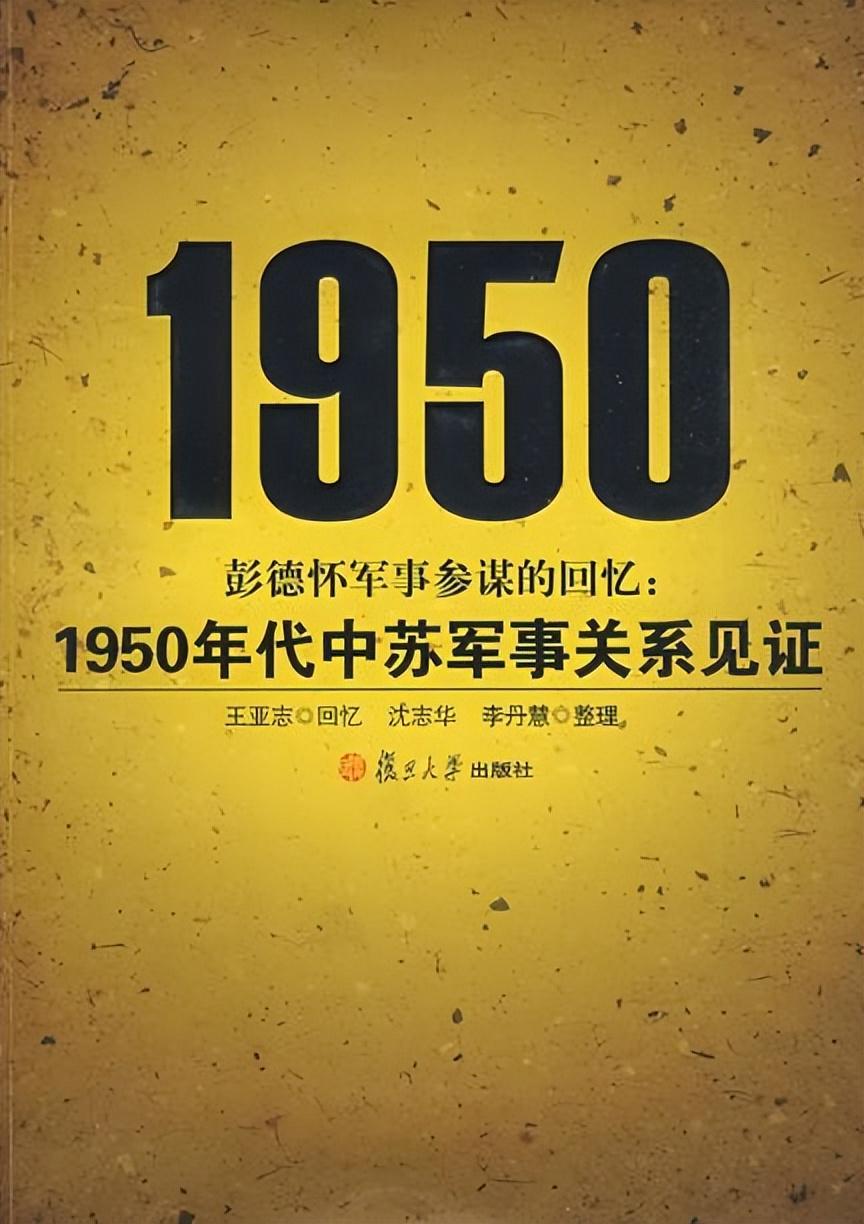
老林为啥犹豫?外界常拿“畏战”说事,其实他打不打首先得能熬夜。早在解放战争东北战场,他就因神经衰弱常常头痛欲裂,甚至提前离开前线去武汉静养。苏联档案也能找到高岗写给莫斯科的求医电报。身体不好是真,谨慎也是真。辽沈战役他对“关门打狗”拖了两天,背地里他爱说一句口头禅:“少死一个师就是胜利。”
然而,谨慎不等于拒绝履职。七月北京开第二次保卫国防问题会议,他当面告诉毛主席:“四野义不容辞,要几个军给几个军。”随后还亲自提议把13兵团黄永胜和15兵团邓华对调,并推荐粟裕当边防军司令。毛主席全盘通过。由此可见,他不是不想干,而是想把提前量做足。

仁川登陆后第三天夜里,彭富九赶到富强胡同的小院。灯下,林彪递给他一纸手令:“技侦局立即抽人组队,随我进朝鲜。记住,就算最后不去,你也不能对外提半个字。”这份保密令直到多年后才在回忆录里浮出水面,说明林彪对“我可能要上前线”这一点,并非嘴上说说。
与此同时,周总理奉命赴莫斯科谈援助。林彪虽身体欠佳,也搭同一班机同行,本意除了看病还有帮总理“压价要货”。谈判桌上,周总理先放了一句“最好还是不出兵”,实际是要诱斯大林增加军援。斯大林回敬:“不出兵,美军顶多一周就到鸭绿江。”摆明是想推中国上场。

谈判卡在空军问题——苏联只愿意“后方掩护”,不能飞过“三八线”。周总理坐在沙发里一句“打仗不能靠木头枪”,气氛降到冰点。宴会上斯大林举杯示好,林彪一句“医生不让喝”敬而不饮。师哲后来回忆,老斯尴尬地笑了笑,“没毒,来一口也行吧?”林彪还是放下杯子,连姿态都懒得做。有人小声嘀咕:“这位瘦将军何以指挥千军?”场面够冷,却真实。

10月12日,北京收到了“中苏一致同意不出兵”的联电。毛主席当天批示“各部暂不出动”,留了个回旋。第二天便派人把彭德怀从沈阳叫回。“你看还打不打?”主席问。彭老总想了足足十分钟,只留下一句:“空军不来就不来,炮可以多要几门,依旧能打。”这句话为会场定了性。
再往后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节点:10月18日晚,邓华接电,四个军夜渡鸭绿江;10月25日,义勇军在两水洞拔掉第一颗钉子。至此,志愿军司令员的人选终于尘埃落定——彭德怀。林彪留在莫斯科继续治疗,直到翌年春天才回国。

假如当日毛主席回电同意“游击战略”,半岛北部也许会出现另一种战法:人民军转上山,中国提供武器,而林彪或许真会以“四野教头”身份到长白山后方建训练营。历史没走那条岔路,不能证明它就是错路,却能说明决策之难——一边是工业差距悬殊的热战,一边是可能漫长无尽的游击。
对于那些亲历抉择的人,很多细节被尘封多年。林彪那张没喝下去的红宝石酒,彭德怀桌上的十分钟沉默,周总理“要枪不要空”的讨价还价,都是那个秋天真实存在的瞬间。人们常说将帅决胜千里,其实决的是分寸:多一门炮还是多一个师,喝一口酒还是放下杯子,差一点,就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