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明宏
编辑|李春晖
1980年,物理学家杨振宁在谈及高能物理未来时,曾抛出一句流传至今的断言:The party is over(盛宴已散)。这句话若用以形容当下荧屏内外的“自嬷”现象,竟意外贴切——当观众刚弄懂“自嬷”的定义(《内娱嬷学初探》),这股热潮已悄然褪色。新词的魔力往往在于其未被完全解构时的吸引力,一旦被反复咀嚼,便失去了最初的鲜活。
自嬷的精髓,在于分寸的拿捏。少一分则显单薄,多一分则显矫饰。以《水龙吟》中的罗云熙为例,其角色虽延续了润玉式的清冷,却少了那份眼神中的破碎感。这种差异不仅源于角色设定,更在于表演者对“自我展示”的把控——当角色过度沉溺于自身脆弱时,便如同陈乔恩版东方不败对镜自怜,非但无法引发共情,反而显得刻意。

当下的影视创作正陷入叙事危机。创作者精心雕琢“完美受害者”,却忽略了观众的真实需求——当剧中人忙于展示伤口时,观众早已转而关注自身的情感投射。那块名为“自嬷”的蛋糕,早已被创作者与观众分食殆尽,留下的只有空洞的表演与疲惫的审美。
《水龙吟》的妆造陷阱与叙事失衡
初看《水龙吟》,难免产生错觉:这是男子十二乐坊的跨界演出?清冷佛子、布袋戏妆容、苗疆少年元素的大杂烩,连罗云熙饰演的唐俪辞都像是美妆博主转行。剧中人个个衣饰繁复,仿佛武林大会需增设“补妆环节”。罗云熙的头冠珠饰过长,转身时竟能自抽脸颊;方逸伦的苗疆造型银片叮当,打斗时宛如莲花落表演;王以纶的奇装异服,更让人怀疑其角色靠收售古着维生。
抛开妆造争议,该剧后半段仍具可看性。方逸伦如阴湿男鬼般纠缠罗云熙,后者则以多智近妖的姿态破解困局。这种布袋戏式的妆容看久了,竟也别有一番滋味。尤其是陈瑶调戏清冷佛子的段落,值得反复品味。

然而,唐俪辞的“自嬷”才是真正危机。婚礼大开杀戒时的陶醉神情,与东方不败夺权成功如出一辙;与雁门少主打斗时,仍不忘整理滑落的大氅。剧中每一个表情、运镜都在呐喊:“看我多美、多痛、多值得怜爱!”这种过度自怜的呈现,将复仇故事沦为主角个人秀,连方逸伦与罗云熙的深仇大恨都成了背景板。
唐俪辞的失忆桥段更显荒诞。方逸伦称其为“小怪物”,张峻宁任其咬伤胳膊而不阻拦。若37岁仍被如此称呼,甜蜜之余不免尴尬。创作者似乎忘记了,美强惨的魅力在于留白,而非将所有情绪明码标价。
从“美而不自知”到“自嬷成瘾”
早期的美强惨角色,如《琅琊榜》中的梅长苏,总带着“美而不自知”的疏离感。病弱身躯下隐藏的坚韧信念,使其角色层次丰富。他自视为游荡世间的残魂,与昔日明媚少年林殊形成鲜明对比。这种自我贬抑,恰是角色魅力的核心。

《香蜜沉沉烬如霜》中的润玉亦是如此。复杂心理与矛盾性格,使其比《长月烬明》中的澹台烬更具深度。作为阴谋产物的他,外表平静下极度渴望温暖,即便登上帝位也难逃孤独。
深度痛苦中的人,鲜有闲心展示伤口。自嬷角色的不讨喜,源于其过早预设观众会爱上自己的脆弱。《藏海传》中的藏海是一个转折点。肖战饰演的角色从不知觉到自我体察,将美貌转化为武器。他会用无辜眼神麻痹对手,被推倒时发出喘息,让人分不清谁是猎物。这种“功能化”的自嬷,尚在叙事平衡范围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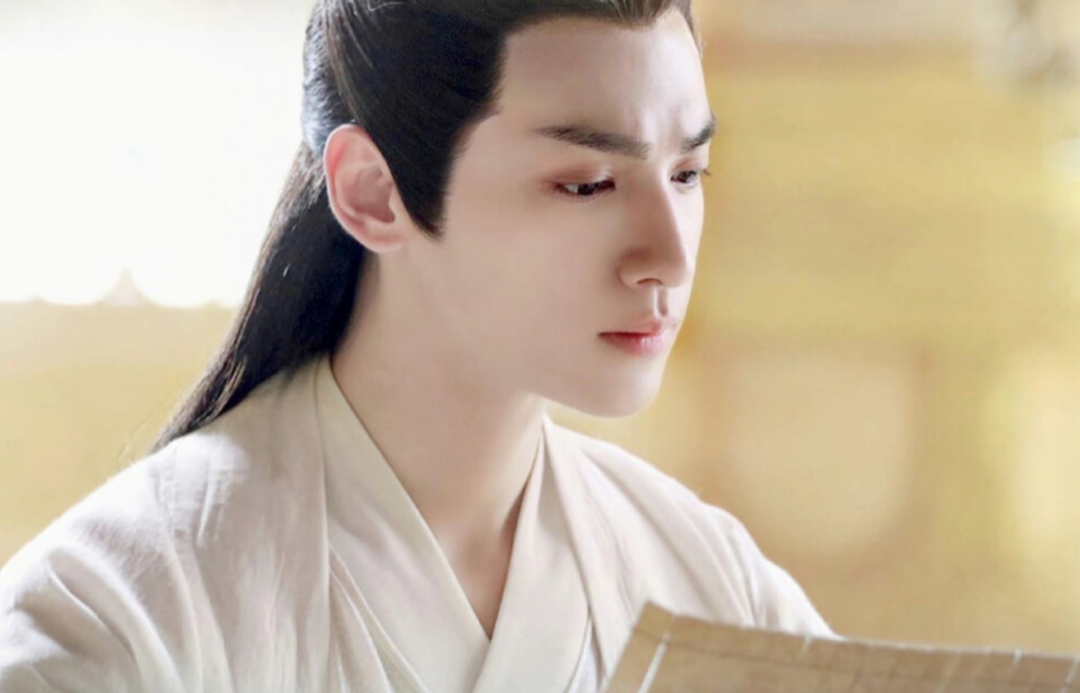
但当主创有意识塑造美强惨时,角色难免向自嬷偏移。悲剧性从“被解读”转向“被告知”,剧集通过大量台词和心理特写,不断释放“应怜爱他”的信号。叙事重心完全转向主角内心世界,故事失去呼吸空间。主要角色膨胀的同时,剧集框架头重脚轻,摇摇欲坠。
大众自嬷:社交媒体时代的心理防御
将痛苦外化为可欣赏的叙事,本质是心理防御机制。观众对角色自嬷的敏感,源于自身生活中自嬷行为的频繁。社交媒体上,“嗲子”撒娇、“娇妻”发癫、“堂哥”诉苦,皆是精心包装的自我创伤展示。
“堂哥文学”的爆红便是例证。一位女士缅怀49岁病逝的堂哥,其创业失败、啃老度日的经历,竟引发网友集体共情。评论区充斥着“天下堂哥如过江之鲫”的感慨,甚至有人续写《我的叔叔于勒》,让于勒给侄儿留20万法郎。这种狂欢背后,是大众对失败者的浪漫化投射——将失败包装为“天命不与”的悲剧,比直面现实轻松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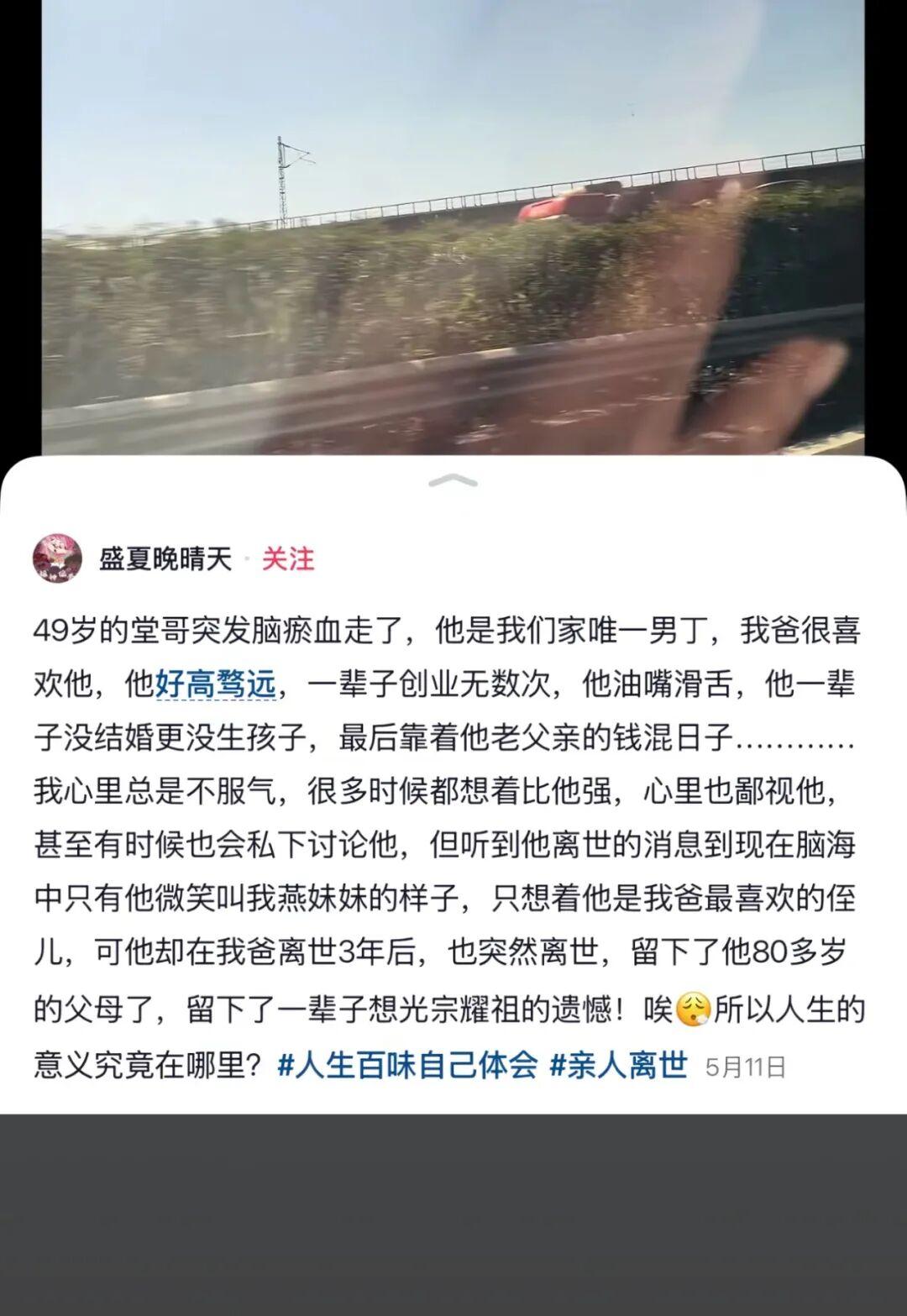
XX文学的兴起,揭示了大众对情感投射的渴望。《剑来》中陈平安的逆袭,何尝不是英雄自怜?“还不曾去过倒悬山”的遗憾,既是书粉的个体记忆,也是网友对未竟之事的集体共鸣。
问题的核心在于,创作者不能包办角色的所有心理活动。当角色的每一个情绪都被剖析得明明白白,共情便沦为填鸭式灌输。高级的共情需要留白,让观众自行填补缝隙。若堂哥自己感慨失败,共情者可能会嘲笑;但由堂妹悼念,行为艺术便升华为互联网文学。

自嬷是年轻人在高压社会与数字媒介下的复杂行为,杂糅了情感诉求与社交策略。为了让观众痛快代入,创作者与主演应退居幕后。蛋糕有限,若先自嬷起来,观众该去何处寻欢作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