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年前,笔者曾在专栏中提出战争片的鉴赏标准:若观影后大众自发前往纪念馆献花默哀,则属优秀作品;若观影过程中观众欢呼雀跃,则暴露出作品宣扬仇恨的副作用。这一理论至今仍适用于多数战争题材创作,但在大屠杀题材面前却需重新审视——因其特殊性远超普通战争题材。
反战是战争片的本质要求,但大屠杀题材激发对恶行的合理恨意,并不必然消解其核心价值。这类作品真正的历史使命,在于通过直面创伤、还原血腥场景,警示人类避免重蹈覆辙。
巴尔干的血色记忆:亚塞诺瓦茨集中营
2020年塞尔维亚导演普雷迪拉格·安东尼耶维奇执导的《来自亚塞诺瓦茨的达拉》,以小女孩视角再现二战期间乌斯塔沙政权对塞尔维亚人的种族清洗。这个由安特·帕韦利奇领导的克罗地亚极右翼组织,在纳粹扶持下建立傀儡政权,推行极端种族主义政策。
亚塞诺瓦茨集中营被称为"巴尔干的奥斯维辛",其独特性在于:这是欧洲唯一不由纳粹直接管辖的大型集中营,且杀戮手段异常残暴——斧头砍杀、铁锤碎颅、匕首割喉等冷兵器成为主要工具。集中营管理者丁科·沙基奇甚至有收集死者眼球的变态癖好,乌斯塔沙元首帕韦利奇曾将整筐眼球作为"战利品"赠予希特勒。

电影中有个耐人寻味的场景:为迎接德国军官视察,沙基奇组织囚犯进行"抢椅子"死亡游戏。当德国军官质问为何针对塞尔维亚人时,沙基奇冷酷回答:"因为他们是塞尔维亚人。"这种基于种族纯净的意识形态,导致部分底层成员甚至杀害自己的塞尔维亚妻子和孩子以表忠诚。
乌斯塔沙的极端政策包括:三分之一异族强制改信天主教,三分之一驱逐出境,三分之一彻底消灭。他们还禁用斯拉夫语系通用的西里尔字母,试图从文化层面抹除异族存在。电影开篇通过小女孩达拉与男孩的对话,揭示了这种荒诞的种族划分标准——仅凭划十字的顺序差异,就足以引发灭族之祸。

学者景凯旋曾指出:"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人会为观念迫害他人。"这种观念驱动下的暴行,在亚塞诺瓦茨集中营的遇难者数字争议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克罗地亚官方统计8.2万人,塞尔维亚方面声称达70万人,而1990年代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为粉饰历史,竟将数字压缩至"最多10万人"。
沃伦惨案:民间暴力的失控狂欢
2016年波兰导演沃伊切赫·斯玛若夫斯基的《沃伦》,被誉为最接近恐怖片的战争题材作品。不同于法西斯系统的屠杀,该片聚焦民间自发暴行——1943-1944年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对波兰人的报复性屠杀导致超10万人死亡。

沃利尼亚地区的民族矛盾可追溯至战前:波兰人虽仅占17%人口,却垄断政府、商界和警界职位。1937年波兰当局推行的"去乌克兰化运动",两年内拆除190多座东正教堂,进一步激化矛盾。电影中乌克兰神父在教堂散布仇恨言论的场景,正是这种长期积怨的爆发。
1943年7月,乌克兰反抗军指挥官克利亚奇基夫斯基下令:"杀掉所有16-60岁波兰男性。"实际执行中,大量妇孺也未能幸免。影片通过肢解、剥皮等极端场景,展现欧洲电影特有的历史控诉方式——相较于好莱坞的克制处理,欧洲创作者更倾向于逼真还原人间炼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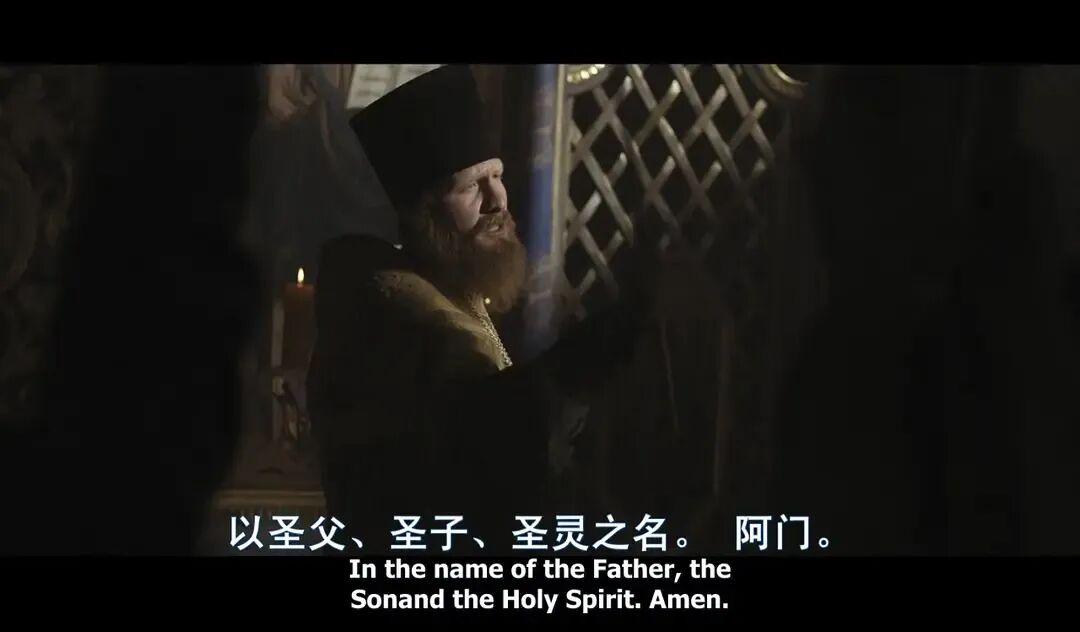
这种暴力循环在电影中得到深刻呈现:抱着孩子的女主为躲避屠杀,竟主动混入德军队伍。当纳粹在特定历史场景中都不再是最残忍的存在,战争的荒诞性便达到了顶点。
历史记忆的争夺战
2018年罗马尼亚导演拉杜·裘德的《罗马尼亚黑历史》,揭露了1941年敖德萨大屠杀——罗马尼亚法西斯政权报复性屠杀3万名犹太人。元首扬·安东内斯库公然宣称:"即使留下千古骂名也在所不惜。"这种态度与日本右翼否认侵华罪行如出一辙。
影片中官员与导演的辩论,揭示了历史认知的困境:当被问及为何只承认特定大屠杀时,官员以德累斯顿轰炸、广岛原子弹为例,试图将历史罪行相对化。这种和稀泥的认知,恰恰印证了大屠杀题材影视的价值——通过影像记录,创造有效的认知途径,打开正确的历史记忆。

从亚塞诺瓦茨到沃伦,再到敖德萨,这些二战期间被主流叙事忽视的暴行,通过影视创作获得新生。它们提醒我们:人类历史上还有太多未被充分认知的屠杀,但认知的有限性不应成为逃避的理由。唯有将历史罪证公之于众,才能有效钳制法西斯幽灵,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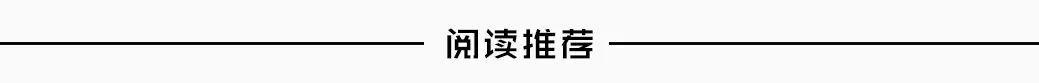
作者:臧否|No.6558 原创首发
开白名单 duanyu_H|投稿 tougao99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