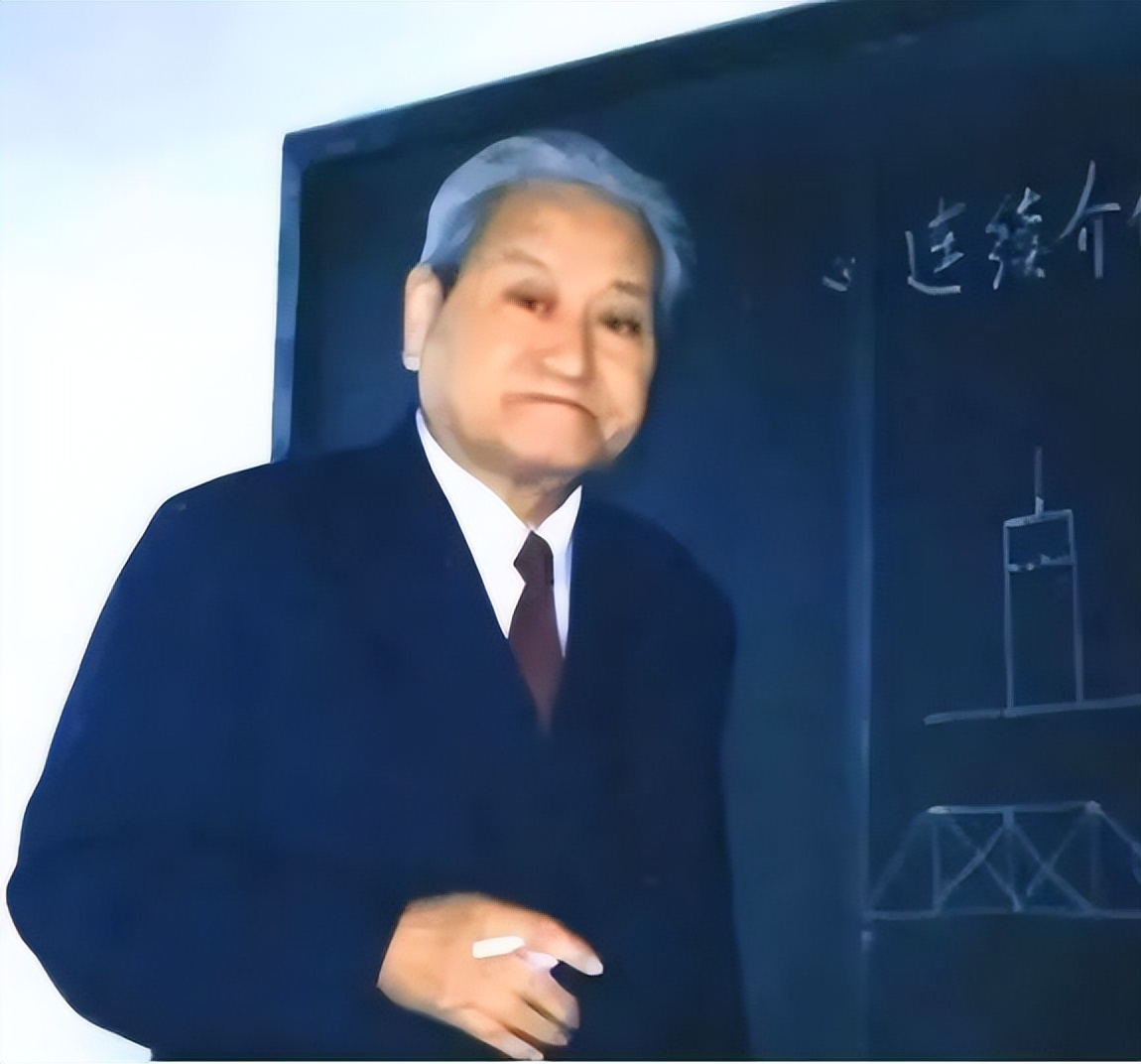“三峡大坝不能建!否则迟早都要被炸掉!”1992年,当长江三峡工程议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时,81岁的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在人生最后一份技术建议书中写下这句振聋发聩的警告。这位与江河博弈半生的水利专家,为何在工程立项前夕发出如此激烈的反对声?二十余年后的今天,他的预言与现实产生了怎样的碰撞?
1992年春,全国人大审议三峡工程议案之际,黄万里将一份长达万言的技术建议书直接递交国务院。开篇即言:“三峡大坝若建成,终将被炸毁,我恳请决策者三思。”尽管这份建议书当时未获公开,但其核心观点在水利界引发持续讨论。支撑他反对立场的,是三个基于长期研究的科学判断。
泥沙淤积:被验证的工程隐患
黄万里根据对长江泥沙运动的长期观测,预言三峡库区将面临严重泥沙淤积问题。他指出,上游来沙将在水库沉积,不仅减少有效库容,更会抬高重庆等上游城市水位,形成“悬河”风险。2003年蓄水后的监测数据印证了这一担忧:2003-2013年间,库区泥沙淤积量达18亿吨,远超设计预期,导致有效库容减少7%。尽管“蓄清排浑”运行方式减缓了淤积速度,但问题依然存在。
生态破坏:特有物种的消失预警
在1992年致学生的信中,黄万里预言大坝将削弱中下游湖泊与长江的水力联系,引发湿地退化,并特别指出“某些特有物种可能会消失”。2019年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报告显示,三峡蓄水后,长江四大家鱼自然繁殖规模下降70%。尽管生态变化存在多重因素,但大坝对水生态系统的爆发性影响已成共识。
战略安全:被低估的潜在风险
黄万里在校内讨论中曾直言:“战争状态下,如此巨大的水坝将成为极其危险的战略目标。”这一观点在当时被视为悲观,但2008年汶川地震后,大型水库诱发地震的讨论再度升温。尽管官方研究认为三峡水库仅引发微小构造地震,但地质作用的复杂性恰恰印证了黄万里生前强调的“不可预测性”。
争议背后的决策逻辑
黄万里的反对是否正确?答案或许不在于对错判断,而在于揭示重大工程决策的复杂性。现实中的水利建设往往是在防洪、发电、生态、安全等多重约束下的权衡。中国政府自2008年起投入巨资用于三峡后续工作,包括地质灾害治理、水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这些补救措施本身即承认了初始决策的局限性。
长江安庆段一位老渔民的感慨颇具代表性:“现在的鱼确实少了,但洪水也没那么凶了。”这种矛盾感受,正是三峡工程效益与代价并存的缩影——它既带来了防洪、发电等巨大收益,也付出了生态、社会等方面的成本。
2001年黄万里逝世时,未能目睹三峡大坝全面蓄水的实景。但他留下的警示依然振聋发聩:在改造自然时,必须保持敬畏与审慎。这种态度在当今重大工程决策中依然珍贵——它要求决策前充分评估风险,实施中持续监测调整,并在事后及时补救。
三峡争论的本质,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永恒命题:既要利用自然造福人类,又要尊重自然规律。像黄万里这样的反对声音,虽非最终决策依据,却为全面评估风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视角。在追求发展的道路上,这种审慎的智慧,或许正是最宝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