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这条自青藏高原发源、绵延6300多公里的巨龙,不仅是中国最长的河流,更是沿岸数亿人口的生存命脉。在长江下游的江阴靖江段,一场持续百余年的地理变迁正在悄然发生——江面宽度从清光绪年间的3.3公里骤减至如今的1.25公里,缩窄幅度达80%。这一惊人变化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自然与人文密码?

长江下游自湖口至崇明岛入海段被称为扬子江,这里江面宽阔、水流平缓,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江阴作为扬子江的起点,自古便是连接上游与河口的关键节点。春秋战国时期,苏北大平原与扬州、镇江以东仍是一片汪洋,仅少数高地露出水面。秦始皇南巡时曾在江阴秦望山驻足,彼时江阴至靖江北侧的江面达到最宽阶段。
三国时期,东吴在北侧沙洲上开辟马洲养马;南朝至唐宋,北面陆地逐渐成形,张家港成为重要出海口;明朝郑和船队正是由此启航。至清光绪年间,江阴黄山至靖江江段宽达3.3公里,利港至夹港段更是有10公里之宽,渡江需耗费数小时。然而,仅仅150年后,黄山至靖江江面已缩至1.25公里,利港至夹港也仅剩5公里。

江面缩窄的主因并非自然变迁,而是人类活动的持续干预。自宋朝起,长江下游人口激增,土地资源日益紧张。为扩大耕地,沿江居民开始大规模围湖造田、围江造圩。所谓“圩”,即通过筑堤排水将滩涂与浅水区转化为农田的工程。江阴靖江一带遍布头圩、顾家圩、三圩等地名,这些名称正是围垦历史的活化石。
明清时期,南京、镇江等地因人口增长导致土地短缺,农民沿江开垦成为常态。20世纪后半叶,连芙蓉湖都被填平,为常州、江阴新增十万亩耕地。围垦使陆地向江心推进,江道自然变窄。历史上著名的黄天荡,本是南宋韩世忠与金兀术交战的宽阔江面,如今已完全成为陆地。这一变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数百年积累的结果,近150年尤为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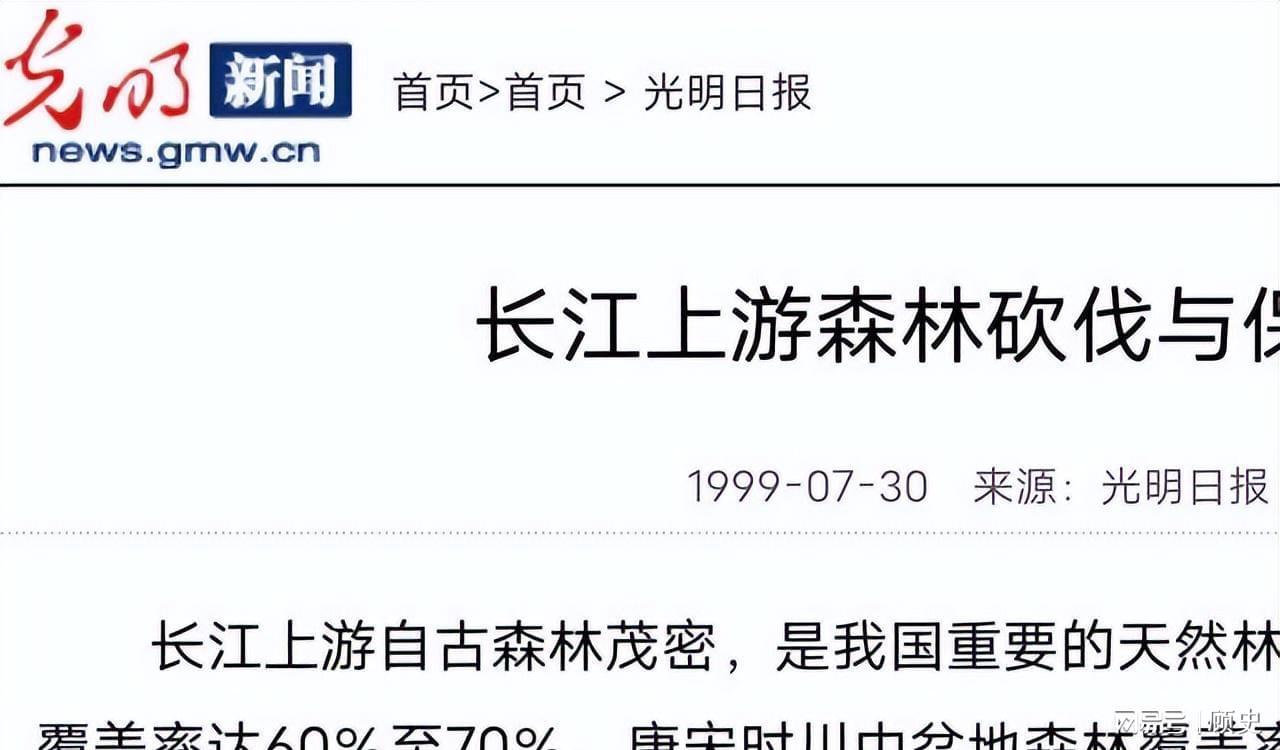
除围垦外,泥沙沉积也起到辅助作用。许多人认为上游四川砍伐森林导致泥沙增多,但实际情况更为复杂。明末清初四川战乱导致人口锐减,随后湖广、福建移民大量涌入,砍林开地与美洲作物(如玉米、番薯)的引进刺激了更多开垦,森林减少引发水土流失,长江泥沙量增加。
清末民国时期,川北、川西再次大规模砍伐林木,泥沙量进一步上升。然而,这些泥沙并未全部抵达下游——三峡工程建成后,泥沙在湖北沉积,洞庭湖、鄱阳湖分流了部分泥沙,安徽、南京段因流速减慢又沉积一部分。真正到达江阴的上游泥沙已所剩无几,下游泥沙主要来自本地河床冲刷,围垦则加速了这一沉积过程。河流下游堆泥沙是常态,如华北平原、珠三角均由此形成,但江阴的变化中,围垦仍是主导因素。

江面缩窄直接导致水位易涨,洪水风险显著增加。历史上,江阴水灾频发: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长江大水,沿岸农田房屋尽毁;1931年夏,水位达4.7米,淹没2.9万亩农田;1991年,37.4万亩稻田被淹,3000亩棉田受灾,5.3万亩鱼塘决口,980多家工厂停产。
洪水来袭时,圩堤若不牢固,损失将极为惨重。围垦虽增加了土地面积,却也埋下了安全隐患——遇大雨则易内涝。如今,上游的葛洲坝(1981年建成)与三峡工程(2003年蓄水)通过调控水流、减少泥沙,结合荆江整治,显著提升了下游防洪能力,水灾发生频率已大幅降低。然而,梅雨季至八月期间,防洪工作仍不可松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