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升起、钟表滴答、四季更替,这些看似平凡的自然现象,其实悄无声息地构成了我们对“时间”的全部认知。
但你可曾想过,如果把你送进一个彻底隔绝阳光与钟表的洞穴,让你在其中度过数月,你还知道今天是星期几吗?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美国NASA的一群科学家,脑洞大开地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人体实验。

他们挑选一位女性志愿者,让她在一个完全没有时间感的地下空间中生活210天,只为回答一个大胆的假设。
如果剥离一切“时间标识”,人类还会感知时间的流逝吗?
然而,这场挑战尚未进行过半,却因被试者的“精神崩塌”戛然而止。
这个实验究竟发生了什么?又为何让一名本性乐观的女子,在130天后身心俱疲、几乎崩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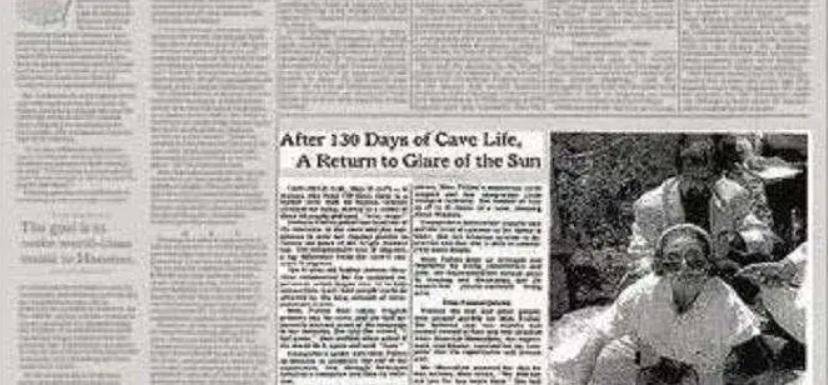
当那扇门“轰隆”一声合上时,27岁的斯蒂芬妮·福里尼正式告别了日升月落的世界,独自走进了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
那是一间藏身于地下三十米的岩洞小屋,远离人声鼎沸的街道、手机的嘈杂提醒,也远离时间最原始的指针——阳光。
20平方米的房间里摆放着床、桌椅、小冰箱和各种生活用品,一应俱全,甚至连电脑、游戏机和几本精挑细选的书籍都不缺。

与普通的居所不同的是,这里没有窗户,光源来自天花板上几盏冷色灯光,每盏灯都是一样的亮度、一样的色温,永远不会调暗,白天和黑夜因此失去意义。
温度维持在恒定的23度左右,氧气输送则通过特殊装置来维持,只为模拟外界最舒适的环境。
科学家们希望,剔除所有影响人类对时间感知的变量,只留下一个“纯粹”的人类个体,在封闭、静谧、单调中自行摸索生活的节奏。

斯蒂芬妮一进来便显得非常兴奋,作为一名室内设计师,她长期在快节奏和高强度的工作中打拼,这次实验对于她而言,更像是一场带薪度假的奇遇。
她洗了一个热水澡,换上一套舒适的运动服,给自己泡了杯咖啡,坐在床边,一边翻看着一本心理学的书籍,一边轻轻哼着歌。
没有人催促她,没有闹钟提醒她睡觉,也没有任务清单等待她完成,一切都由她自由掌控。

之后的几天,她尝试用纸笔记下每天完成了什么事情,在没有钟表和阳光的日子里,斯蒂芬妮构建了属于自己的生活秩序。
她为自己定下了一个小目标,哪怕在这个“无时间”的环境中,也要像在正常世界一样有条不紊地生活下去。
每完成一个小任务,她都会在纸上画个记号,那些密密麻麻的符号,在她眼里是“自律”的证明,也是“时间流逝”的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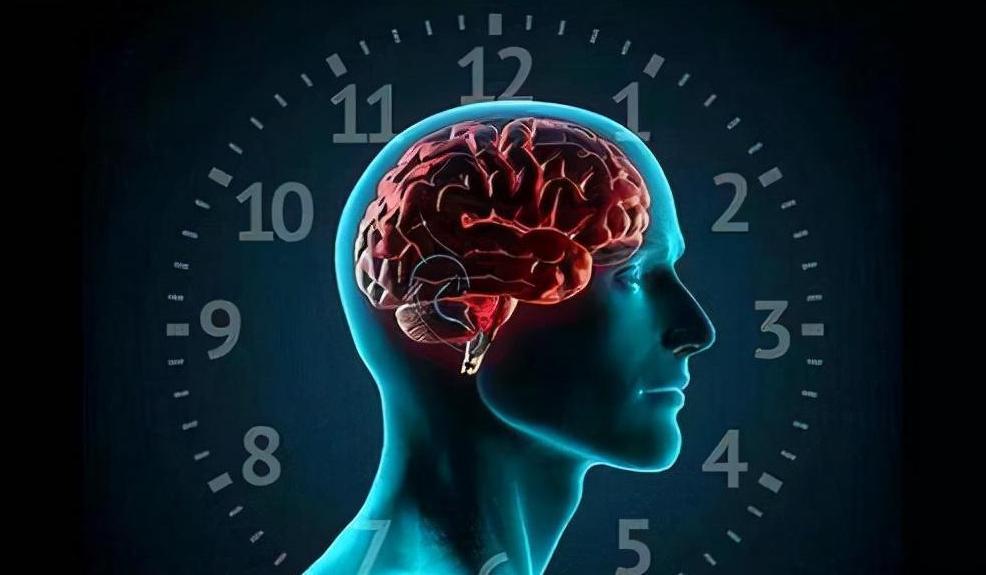
实验的前十天,科学家们观察她的状态,纷纷表示“超乎预期”,饮食规律、精神稳定,连睡眠周期也未出现明显波动,很难想象她已经脱离了“时间社会”。
但这种顺利的表面之下,始终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微妙变化,科学家们同样注意到,她对“标记”的依赖在悄然加剧。
斯蒂芬妮开始频繁检查自己的笔记本,确认有没有遗漏,在进食前会反复犹豫是否该吃这顿饭,甚至会因为某个任务没有完成感到情绪低落。

那时的她并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里,她将一步步走入时间的迷雾深处。
起初,斯蒂芬妮用不同颜色的笔记录每一类活动,让这个时间空白的世界看起来不那么无序,
可她并未意识到,秩序本身就来自时间。
当外部时间彻底被剥离,内心所依赖的节奏感也将逐渐瓦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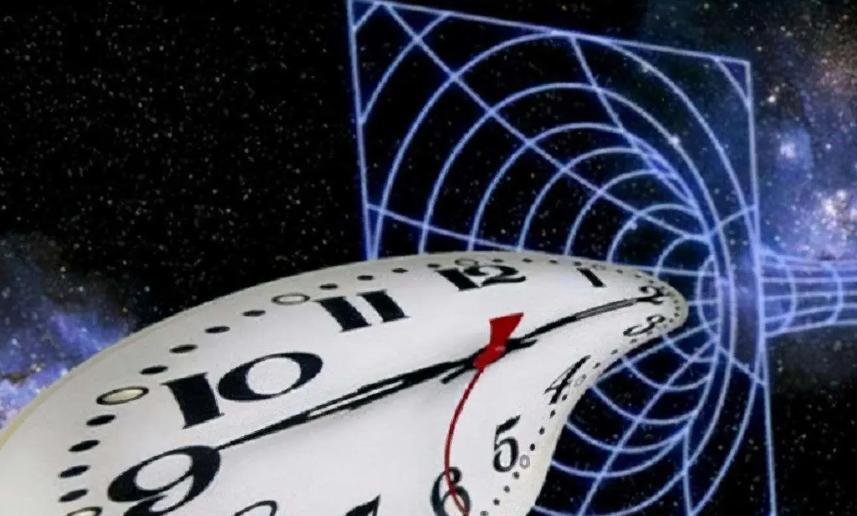
曾经规律的“睡醒—吃饭—读书—娱乐”循环被打破,她开始感到疲惫,明明刚睡醒却头晕眼花,打着游戏突然眼皮沉重,不知不觉倒在沙发上,一觉醒来已是“另一个时间”。
她曾经用身体的感觉来判断时间,比如肚子的饥饿、眼睛的酸涩、肌肉的疲劳,但现在,所有的身体信号都在捣乱,她会在不饿的时候进食,在极度疲惫时却无法入眠。
监控画面中的斯蒂芬妮,渐渐变得不再活跃,面对电脑更多是在发呆,睡着后的姿势不自然,似乎随时可能惊醒,脸上不再有笑意也不再哼歌,生活开始呈现出一种诡异的节奏。

科学家们从摄像头看到这一幕时,神情凝重,他们知道,人类的内在节律(生物钟)依赖于日光与时间标记的同步刺激,现在这些全都被拿掉了,她的身体正在进入“混乱模式”。
最令人担忧的是,斯蒂芬妮不再提笔记日,那本曾经被她当作“生活锚点”的笔记本,被她扔进了垃圾桶。
“写也没用,我不知道自己是写给谁看。”

这个阶段,斯蒂芬妮的人格边界开始变得模糊。她不是不想维持正常生活,而是已经不知道“正常”意味着什么。
日子像是泡在一锅混沌的汤里,她无法判断什么时候该清醒,什么时候该休息,什么时候该感到开心,什么时候该对着镜头微笑。
而这一切的源头,仅仅是因为她看不到太阳,也无法得知现在是几点。

当科学家们注意到,斯蒂芬妮与设备端的工作人员互动频率越来越高,每当电脑亮起,她就像孩子看见母亲的灯光一样兴奋
为了缓解她日益加剧的孤独情绪,实验团队决定打破一点原有的“封闭规则”,为她找来了一位“通信朋友”,一个生活在实验基地附近的9岁小男孩。
他的任务很简单:每周通过文字或语音与福里尼分享一些生活趣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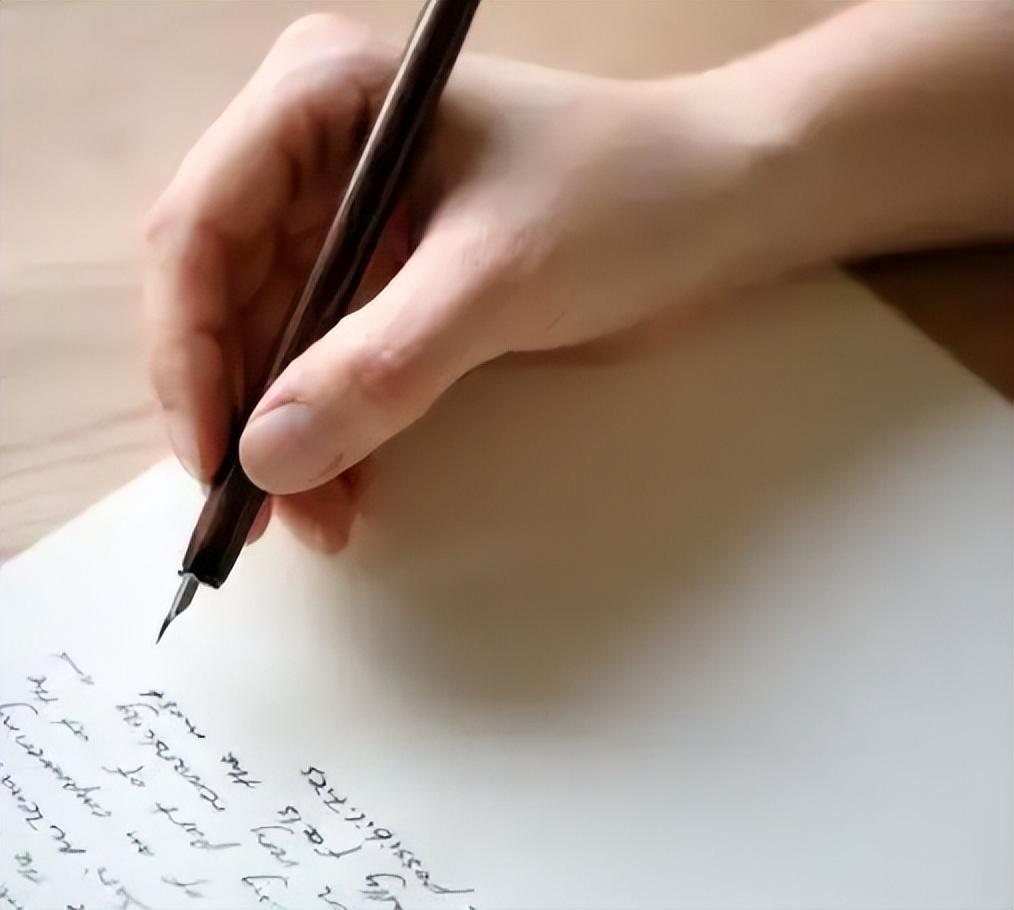
起初,斯蒂芬妮感到无比兴奋,在回信中画了几只想象中的动物,给它们编故事,还给男孩写了一首没有韵律的“地下诗”,对方的童真成了她为数不多的慰藉。
与此同时,实验室为她送去了一把木吉他和两只宠物老鼠,那段时间,她会一边弹吉他一边对着两只小老鼠唱歌,用奶音模仿它们的回应,然后笑得像个孩子。
可是,这些“连接”并未真正止住孤独的侵蚀,大约从第八十天起,斯蒂芬妮的信件内容开始变得模糊不清,错字连篇,她不再讲故事,也不再回应男孩的问题。

她的眼神失去了光泽,说话像在咀嚼空气,甚至开始对设备发脾气。
“你们是不是都不是真实的,是不是我死了,只是没人告诉我?”
她的行为也出现了异常,有时会把墙上的插座贴上便签纸,写着“出口”、“阳光通道”之类的词句,有时会躲进床底下,一呆就是几个小时,说那里“声音比较温暖”。
监控录像记录下,斯蒂芬妮从“自我管理的理性人”,逐步变成一个被幻觉和无意义重复支配的灵魂,生活空间开始被她重组,桌子被推到墙边,椅子垒成奇怪的堆叠等等。

她几乎不再进食,只靠喝水维生,脸色蜡黄、四肢消瘦,曾经圆润的下巴变得棱角分明,科学家们明白,再继续下去,她的精神可能彻底崩溃。
实际上,斯蒂芬妮是个极其注重外在仪态的女人,刚进入实验舱时,她每天固定洗澡,穿着整洁,甚至会在镜前给自己编辫子。
“不管有没有人看,我也要让生活有点尊严。”

可到实验的第100天,那些仪式感早已成了尘封的过往,她已经很久没洗头了,头发蓬乱得像一团掺着油渍的干草,垂在脸颊两边,将她眼角的疲惫遮得严严实实。
科学家们发现,她的体重在短时间内锐减十七公斤,最严重的一周,几乎每天都在掉秤,生理周期也被打乱,原本规律到几乎精准的月经,在进入第四个月后突然中断。
生理节律的紊乱只是冰山一角,斯蒂芬妮的睡眠模式也彻底崩坏,曾经会在“体感夜晚”时自动入睡,如今可以连续清醒三十多个小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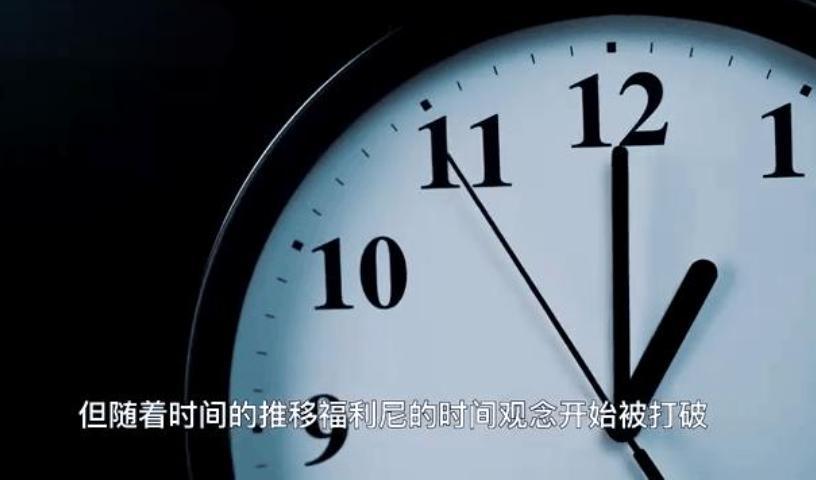
她不再设置起床的“心理闹钟”,也不再试图维持节律,生活已经变成了一场失速的列车,谁也不知道下一站是梦境还是虚无,更可怕的是,她的感官正在退化。
有一次,她端着热水杯,却皱起眉头,声称没温度,这种变化让科学家意识到,她的中枢神经可能正在对外部刺激失去响应能力。
斯蒂芬妮对声音的反应也变得迟钝,以前,外界发出的系统提示音一响,她就会抬头回应,现在要等好几秒,甚至根本没有反应。

行为变得机械而重复,曾连续三天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椅子转一个方向,又在傍晚时分把它们调回原位。
对着电脑屏幕点开纸牌游戏,但不是真的在玩,只是在不停地点击开始—结束—开始,仿佛程序里的每一次重启,是对自己身体的一次救赎。
科学家最终做出决定,中止实验。
斯蒂芬妮被轻声唤醒,身体几乎虚脱,眼神空洞,像是一具被程序写坏的人偶,睁眼看见几位陌生的工作人员站在她面前,第一反应竟是愣愣地问。

“你们……是哪一关的关卡?”
她被送上地面的那一刻,阳光透过地面开口洒进来,洒在她脸上,她的眼睛猛地一眯,随即整个身体颤了一下,像是被突如其来的现实灼伤。
她的身体无法立即适应正常生活中的光与声,在体检室里,不愿说话,只是把身子蜷在靠椅上,像极了一只在寒风中冻了一整晚的小兽。
医生发现她的心率异常、激素水平紊乱、基础代谢下降,还有明显的神经紧张反应,最惊人的是,当工作人员告诉她她已经待了130天时,她沉默良久,最后缓缓吐出一句。

“我以为才刚过两个月。”
在那个无钟表的洞穴里,时间没有带走斯蒂芬妮的生命,却把她的身体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剥去了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