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鹏远
发于2025.10.27总第1209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在中国当代文坛,作家路内以其独特的创作方式与深刻的社会洞察力独树一帜。他写小说从不列提纲,无论篇幅多长、人物多众、故事多复杂,仅凭脑中构思便动笔,却在创作周期的把控上精准如钟表匠人。这种看似随性的创作方式,却让他能在灵感奔涌或陷入困顿时,始终将作品完成时间控制在预期范围内。
2025年除夕,路内完成了酝酿十年的长篇新作《山水》。这部预计一年完成的作品,实际耗时十四个月。当他合上电脑时,发现自己已迈过50岁的门槛,正式步入中老年作家行列。"这是我50岁后完成的第一个作品。年轻时若匆匆落笔,故事或许同样精彩,但既然未写,便是命运安排。"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坦言,"未来,我可能不再写这类历史题材。"

家族记忆:从传说到文学
《山水》以1936年至1996年为时间轴,讲述司机路承宗的一生。这个姓氏的选用并非偶然——路内上一次使用"路"姓命名主角,还是"追随三部曲"中的路小路。那个混迹技校、工厂与社会的青年,常被视为带有自传色彩。而路承宗的原型,则是路内的祖父:一个洋车夫的儿子,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学会驾驶,为杜月笙的学生、台湾银行苏州分行行长开车,甚至将车开到抗美援朝战场。
"他是民间的支援司机。"路内回忆,当时上海汽车多,去的司机也多,不少牺牲在异国他乡。祖父曾险些丧命:美军飞机锁定他开的卡车,来回俯冲数次却未攻击。这些故事,路内从小听父亲、叔叔、姑姑讲述,但5岁丧祖的他并未深想。直到2014年,一位影视朋友想写抗美援朝剧本,与他聊起卡车型号(苏联吉斯、美国道奇),他才首次将家族记忆与文学创作联系起来。
然而,仅凭零碎的家族传说远不足以支撑长篇。路内查阅大量亲历者回忆录,观看黑白电影,试图还原民国时期的语言腔调。这是他首次触碰历史题材——此前六部长篇,文学时空始终未溢出现当代疆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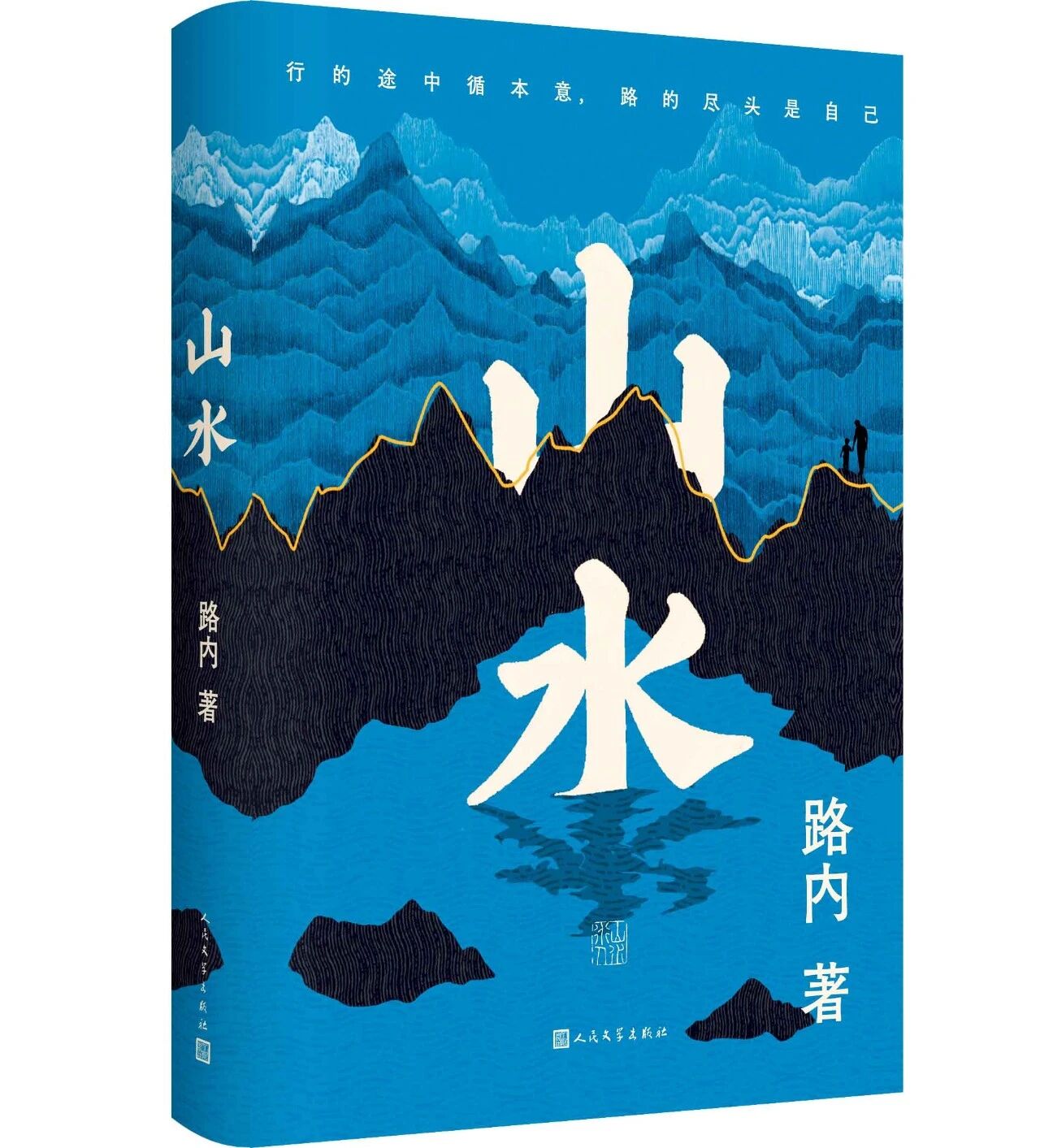
时代切片:从个体到史诗
2015年,42岁的路内决定先写《雾行者》。"那个小说更长,可能会吃掉我四五年的精力。"触发这一决定的,是一位朋友讲述的卧底记者经历:从前如何冒用身份调查,那些仿若谍战的惊险背后,是一个时代特质的消逝。"如果不抓紧记下来,就要彻底被遗忘了。"
他想起1998年第一次远行:在重庆当仓管员时,公司要求他顺便调查销售员卷货潜逃案。到重庆后,他发现混乱远不止于此:仓管监守自盗,销售被皮包公司骗得货款两空。"今天的火车站是最安全的地方,因为有无数探头;但三十年前,火车站却是最乱的地方。这就是中国的变化。"
但路内也怀念那个年代:流动、重组、野生、向上。若非那个时代,他或许仍是国营糖精厂的工人,终日三班倒,住在工人新村。"那个年代的状态很难用词概括,只能通过几个同龄角色,追忆一代人的无聊、躁动、梦想与伤感。"
这种面向时代的写作,从《少年巴比伦》便已开始。"我已强烈感受到变迁的迅速:大量工厂拆除、工人新村推平。环境消失后,自然会产生对个体生命经验与时代的困惑。"作家阿乙曾评价:"路内的作品是从社会和时代里切下来的。"
创作困境:从分散到核心
在《山水》中,路内想讲很多:以汽车象征中国对现代化的百年渴求;借师徒、父子关系展现现代化过程中的观念变化;探讨从清末至今中国历史的秩序崩溃与重建。"但这些想法太分散,需要一个贯穿的核心。"他拒绝让小说成为历史的依附:"真正的历史小说必须处理政治问题,否则只是历史的花边。"
写完《雾行者》后,他陷入创作困境:42万字的体量让他作息紊乱,疫情又带来情绪低谷。2021年,他转而写《关于告别的一切》,却仍无法摆脱《雾行者》的影子。直到2023年,他看到王朔的《起初》:"非常像史诗,但又带有强烈的作者风格,妥妥的反史诗的史诗。我觉得这样很好,我也可以写一个反向的小说,就写一个家庭,触摸历史的注脚。"
最终,他将分散的想法归于人情世故:"人生和命运本身已是一种沧桑的轨迹与进程——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历史的一种动力。"叙事方式上,他打破线性结构:奇数章节话往昔,偶数章节写近前,两条线索各自推进。
文学修行:从长篇到短篇
《山水》交稿后,路内进入"空窗期"。他计划写两个题目:一是将故乡苏州的弹词书目《三笑》改成白话,如同张爱玲重写《海上花列传》;二是关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第一代白领,写他们在无职业经验的情况下如何投入时代洪流。
"过了50岁,应该进入另一种状态。"他引用古话:"人生五十,而知天命。文学也一样,慢慢地什么都会变得不重要,而只是一种自我修行。"他计划60岁前保持稳定写作状态,再出两三本作品,然后"干点别的"。"我倾向于写得再短一点,不要再写30万字以上。年纪上去了,一天写1000字已经脑力跟不上了。小说的好坏不以长短作评判。"
他甚至想尝试短篇:"一直也没好好处理过这一体裁,除了《十七岁的轻骑兵》,总共就只发表过一次短篇。"1998年,他辞掉仓管员工作,将远行见闻写成5000字小说,发表在《萌芽》上,拿到200元稿费。但此后陷入失语,直到2006年母亲突发脑梗过世,他在悲伤中重新拾笔,两个月写出18万字,取名《少年巴比伦》。2007年,该作登上《收获》杂志,他站在天桥上看着自己的名字,终于确定:"我可以成为一个作家。"
《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第39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