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7日凌晨,数千枚火箭弹划破以色列夜空,这场被以色列称为建国75年来最黑暗的袭击,造成1195人死亡、251人被劫为人质。发动这场震惊世界袭击的组织,正是从加沙难民营崛起的哈马斯。这个让中东最强军事力量措手不及的组织,究竟有着怎样的起源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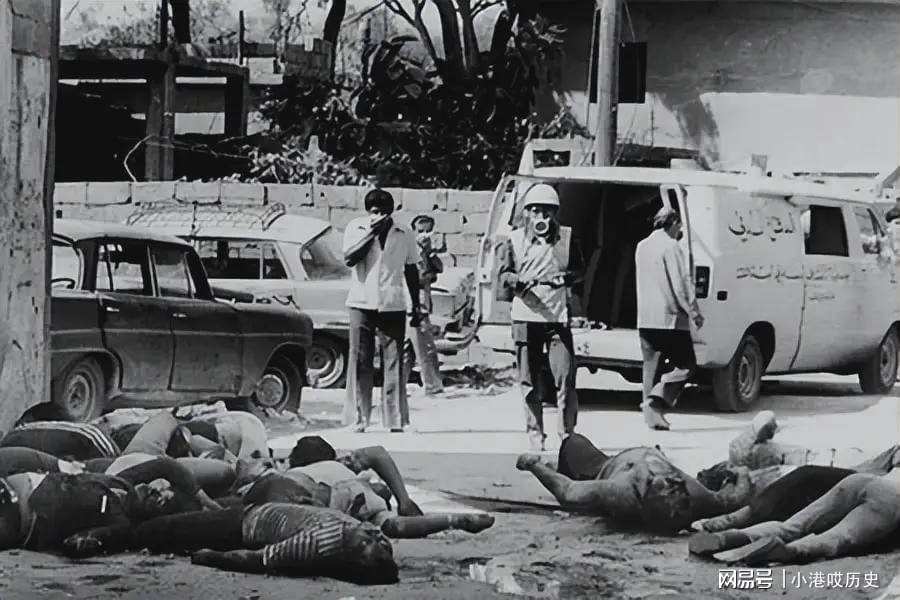
1987年12月8日,加沙地带发生一起改变中东格局的交通事故——一辆以色列军车撞死四名巴勒斯坦工人。愤怒的人群开始投掷石块,没人想到这起事件会引发持续四年的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在这场起义中,坐着轮椅的宗教学者谢赫·艾哈迈德·亚辛看到了机会。
作为穆斯林兄弟会在加沙的核心人物,亚辛自1950年代起就通过开办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将这个埃及起源的宗教组织渗透进巴勒斯坦家庭。但当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导着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控制着政治话语权,穆斯林兄弟会被边缘化。大起义给了宗教势力参与武装斗争的借口。
1987年12月10日,哈马斯正式成立。其阿拉伯语全称"Harakat al-Muqawama al-Islamiyya"意为"伊斯兰抵抗运动",缩写"Hamas"在阿拉伯语中意为"热情"。1988年8月18日发布的《宪章》第六条明确宣称:"哈马斯致力于高举真主的旗帜,覆盖巴勒斯坦的每一寸土地"。第十一条更直接指出:"巴勒斯坦土地是伊斯兰宗教基金,为穆斯林世代所有,直到审判日"。这标志着巴以冲突被彻底宗教化。
与法塔赫的世俗民族主义不同,哈马斯建立了独特的组织架构:表面上有政治部门和社会服务部门,但核心是军事部门"泽丁·卡桑旅"。这个以1930年代反英抗犹英雄命名的军事组织,从诞生第一天起就选择了武装斗争道路。1989年9月,以色列政府宣布哈马斯为"非法组织",但此时这个组织已在加沙深深扎根。

2004年3月22日,一架以色列阿帕奇直升机发射的地狱火导弹,终结了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的生命。26天后,继任者阿卜杜勒·阿齐兹·兰提西同样死于以色列的"定点清除"。两任领导人在一个月内全部身亡,哈马斯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
1963年出生在谢赫拉德宛难民营的伊斯梅尔·哈尼亚站了出来。这位实用主义政治家做出了大胆决定:哈马斯要参与政治选举。2006年1月25日,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哈马斯获得74个席位,远超法塔赫的45个。这个被美国、欧盟定义为"恐怖组织"的政党,通过民主选举上台了。
但好景不长,西方国家立即切断援助,法塔赫拒绝交权,两个巴勒斯坦政党爆发内战。2007年6月,加沙地带爆发激烈冲突,五天内哈马斯彻底控制该地区。从此巴勒斯坦分裂:法塔赫控制约旦河西岸,哈马斯统治加沙地带。
哈马斯的权力结构远比表面复杂。其最高权力机构是政治局,主席才是真正的一号人物。这个位置长期设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因为留在加沙的领导人随时可能被以色列暗杀。首任政治局主席哈立德·迈沙阿勒在多哈遥控指挥17年,2017年卸任后由哈尼亚接任。但在加沙的实际控制者是更危险的叶海亚·辛瓦尔——这个亲手处决过数十名"叛徒"、建立哈马斯内部安全机构的强硬派人物。2024年7月31日哈尼亚在伊朗遇刺后,辛瓦尔于8月6日被任命为新的政治局主席。

维持哈马斯庞大军事开支的资金从何而来?这个被国际社会制裁的组织,有着复杂的地缘政治资金链。1992年,哈马斯在伊朗找到了重要金主。尽管哈马斯是逊尼派、伊朗是什叶派,但现实政治超越了宗教分歧——伊朗需要哈马斯在以色列南部制造压力,作为回报每年至少1亿美元资金通过地下隧道流入加沙。
卡塔尔是另一个公开支持者,2012年卡塔尔埃米尔访问加沙时承诺4亿美元援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多次为哈马斯站台,其领导人迈沙阿勒曾在安卡拉受到国宾级待遇。这些资金用于卡桑旅的火箭弹、隧道和训练基地,也支撑着医院、学校等民生机构——这是哈马斯获得民众支持的基础。
真正让哈马斯强大的,是以伊朗为核心的"抵抗轴心"军事联盟。这个包括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也门胡塞武装和哈马斯的联盟,有着共同目标: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的影响力。伊朗的战略是通过代理人组织施压,而非直接与以色列开战。
武器运输路线复杂得令人震惊:伊朗制造的武器通过海运到叙利亚,再陆路到黎巴嫩,最后通过地下隧道到达加沙。尽管以色列空军经常轰炸运输车队,但总有漏网之鱼。卡桑旅的火箭弹技术因此不断提升,从最初射程几公里的土制火箭,发展到现在射程超过100公里的"卡桑"系列导弹。

哈马斯将巴以冲突定义为宗教战争,认为巴勒斯坦土地是"伊斯兰宗教基金",任何放弃都是对真主的背叛。这与法塔赫等世俗民族主义者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可以接受"两国方案",在1967年边界基础上建立巴勒斯坦国,但哈马斯要求的是从约旦河到地中海的全部土地,认为以色列必须消失。
这种立场使任何妥协都不可能。哈马斯不是传统政党或军事组织,而是一个"全社会组织"。在加沙,它管理着医院、学校、清真寺和市场,230万加沙人的生活依赖哈马斯。这意味着哈马斯投降将导致整个加沙社会崩溃。更重要的是,哈马斯的权力基础是武力而非选票,一旦失去武装就失去一切。
外部支持也强化了哈马斯的抵抗决心。伊朗不会让哈马斯投降,因为这将使其在巴勒斯坦的影响力归零。只要哈马斯继续战斗,资金和武器就会持续流入。从成本收益角度看,战斗比投降更划算。
生存本能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哈马斯高层都清楚,投降意味着死亡——以色列不会放过任何一个领导人。辛瓦尔在监狱里关了22年,出狱后只有继续战斗或死亡两个选择。既然投降也是死,为什么不战斗到底?
心理因素同样重要。哈马斯相信时间站在自己一边:以色列面临人口结构变化(阿拉伯人生育率高、犹太人生育率低),国际舆论也在发生变化,年轻一代对以色列的支持在下降。他们认为只要坚持下去,就能等到转机。
哈马斯不是一个理性行为体,而是一个宗教化的政治组织,按照独特的逻辑运行。只要这种逻辑不变,战争就不会结束。这个从难民营走出的组织,用宗教信仰和生存意志,在中东这个火药桶中持续燃烧着抵抗的火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