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品如(高珊珊)驾驶着车辆,眼神坚定。她已不再是那个在洪家受尽欺负的柔弱妻子,而是归来复仇的美艳女子。这个经典画面,不仅成为《回家的诱惑》的标志性镜头,更预示了未来十余年国产大女主剧的叙事模板——女性觉醒必须以‘丧偶’为前提。
作者| 冼豆豆
编辑| 晶晶
排版| 苏沫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文章发布初始时间:2025年9月24日
‘为所有爱执着的痛,为所有恨执着的伤……’《回家的诱惑》主题曲响起时,观众便知道,那个被丈夫背叛的女人即将开启逆袭模式。这部2011年的爆款剧,用52集篇幅构建了一个主妇重生的经典范式:女主必须在遭遇伴侣背叛或丧偶后,才能触发独立觉醒的副本。

从《那年花开月正圆》中丈夫早逝的周莹,到《我的前半生》里被出轨的罗子君,再到《灼灼韶华》中丧偶出走的褚韶华,国产剧不断重复着同一套叙事逻辑:女性觉醒必须以‘精神丧偶’或‘肉体丧偶’为起点。这种模式在近期热播的《灼灼韶华》中达到新高度——褚韶华在丧偶后,先后与初恋情人夏初、第三位伴侣闻知秋展开感情纠葛,实现事业与情感的双重成长。
节奏加快是当下大女主剧的显著特征。孙俪主演的《蛮好的人生》中,女主胡曼黎仅用前几集就完成从发现出轨到果断离婚的心理蜕变,而十三年前的《回家的诱惑》需要十几集铺垫才开启逆袭模式。但节奏变化未改变核心套路:‘出轨/死老公’始终是大女主剧本的标准开场。

这种叙事背后隐藏着危险的逻辑:女性在有伴侣时无法实现真正独立。仿佛女主必须先‘丧偶’才能找回主体性,而一旦进入新关系又迅速依赖男性扶持。《灼灼韶华》中的褚韶华、《我的前半生》中的罗子君,甚至《绽放的许开心》中的单亲妈妈许开心,都在证明:所谓大女主叙事,始终难以摆脱对男性的依赖。
更矛盾的是,剧集一方面要求女主与家庭切割,另一方面又迅速安排新感情线。这种‘既要又要’的叙事,暴露出创作层面的割裂感——口口声声喊着‘厌男’,却始终让男性成为女性觉醒的助推器。当大女主必须通过‘丧偶’才能证明独立,这种模式化陷阱反而强化了性别刻板印象。

这种叙事割裂在现实中亦有投射。2023年上野千鹤子秘密结婚的消息引发争议,部分网友认为女性主义学者不应走入婚姻。上野在《15个小时的新娘》中回应:登记结婚主要是为友人提供临终照护,并强调‘自己不是什么一个人生活、不婚的教祖’。这位日本女性主义代表人物的观点清晰:女性主义是追求自由的思想,只要自由自在地活着,怎样都可以。
国内同样存在类似争议。Papi酱因孩子随父姓被骂‘婚驴’,麦琳在《再见爱人》中遭遇镜头霸凌,画家曾孝濂的妻子张赞英在《十三邀》中直言‘这辈子困在这个地方’,这些案例反映出互联网语境对女性的极端期待——要成为独立女性,就必须断情绝爱、不婚不育。

但上野千鹤子指出:个体要对自己的衰老和死亡负责,但当一个人老去,不应该害怕依赖别人。这种观点对思考女性独立与关系具有启发意义——感情、婚姻和事业,在女性的人生中不必成为反义词。完全否定家庭主妇的价值,只肯定事业女性的价值,本质是另一种‘极权’。
当前大女主剧的困境,源于‘女性主义等于不婚不育’的二元对立观点。这种思维导致剧集必须在‘丧偶’和‘独立’间二选一,仿佛女性一旦沾上爱情结婚生子就走进命运坟墓。但真正的‘女本位’不应是拒绝男性,而是在有伴侣的情况下也能保持主体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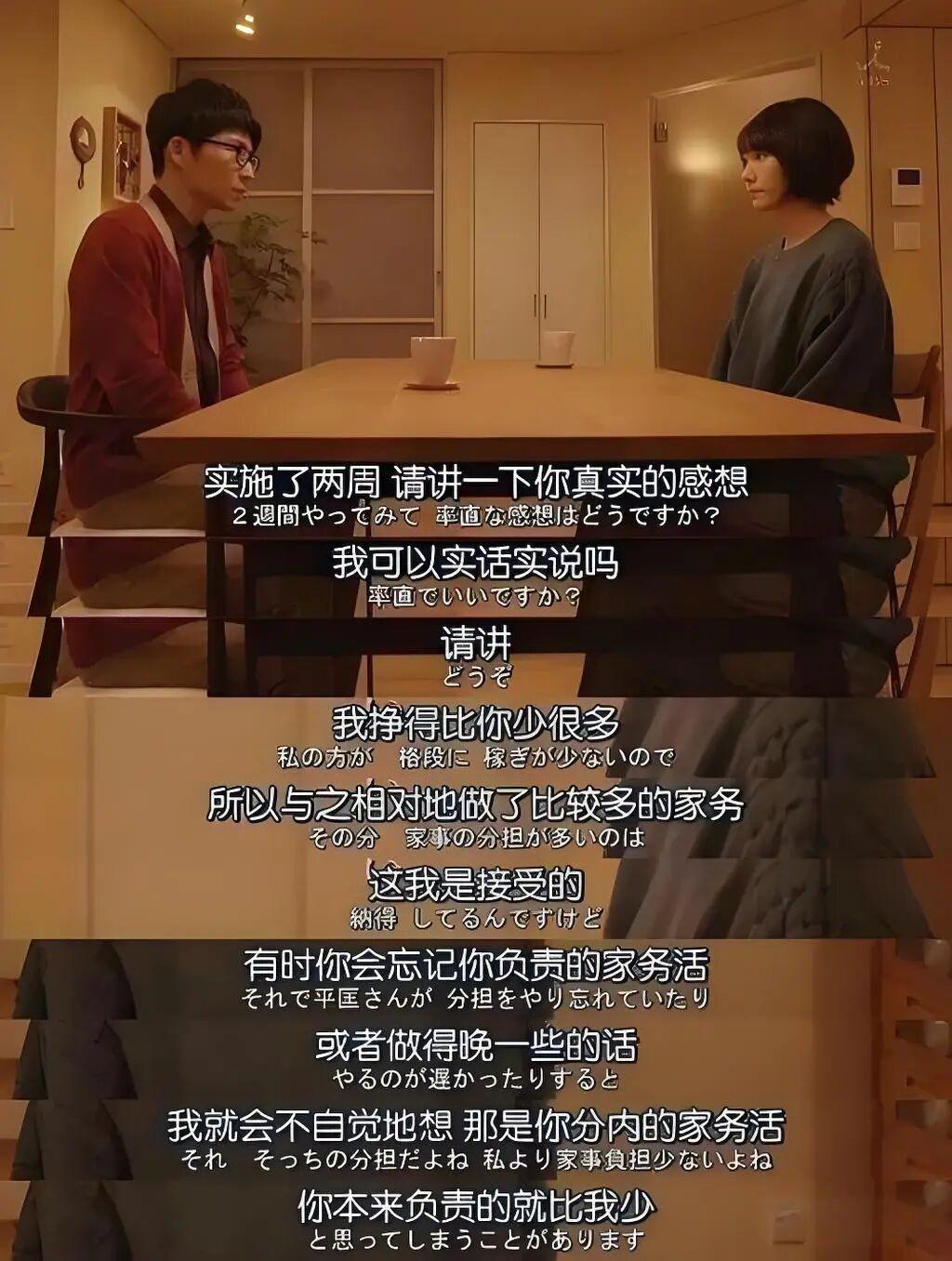
未来女性向剧集需要探索新路径:展现女性在不割裂关系网络的情况下实现自我价值。男人可以是生活中的伴侣、事业上的合伙人,关键是女性无论是否有伴侣,都不应丧失精神独立。允许女性既拥有爱情又拥有事业,既选择婚姻又不丧失自我,才是更为进步的叙事。
正如上野千鹤子在纪录片《最后一课》中的定义:‘女性主义,就是追求一个能让弱者得到尊重的社会。’这一理念也应适用于我们对女性和女性剧集的期待——不再苛求每位女性都必须绝情断爱才能证明独立,也不再对世俗标准里的弱势群体进行价值审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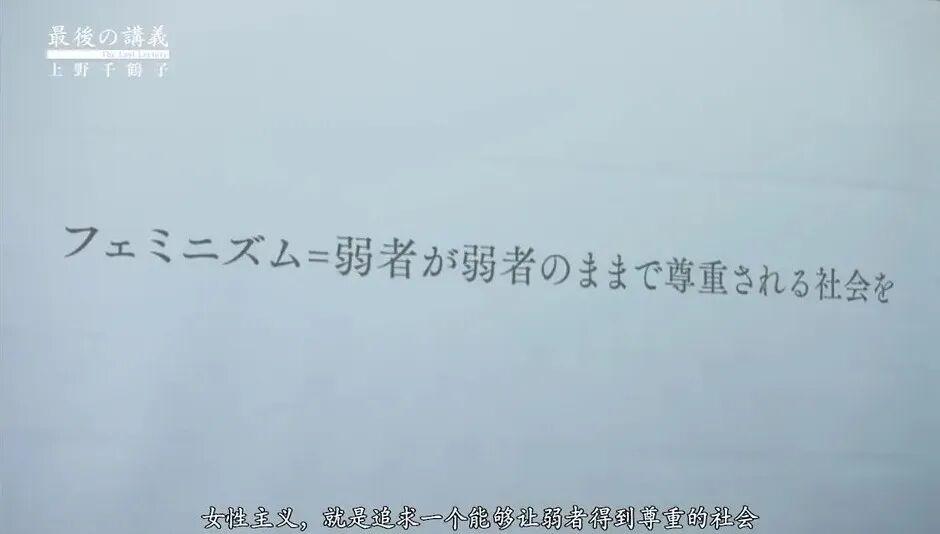
真正的女性主义不是要求女性必须独立、必须符合成功学的期待,而是允许女性自由选择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无论她想成为事业女性、家庭主妇,还是选择不定义任何身份,都应得到尊重。毕竟,女性主义的核心从来不是制造新的枷锁,而是打破所有束缚自由的枷锁。
「四味毒叔」
出品人|总编辑:谭飞
执行主编:罗馨竹
联系邮箱:siweidushu@126.com
微信公众号lD:siweidush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