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专业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古代民族史,本文摘编自《有所不为的反叛者:批判、怀疑与想象力》,特此分享。

几年前,我有幸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一年。那里有一位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1923—2020),他是一位特立独行、激进且具有开拓性的科学家,为现代物理学基础做出了重大贡献。尽管已90多岁高龄,他仍坚持每天到办公室上班,撰写文章并进行演讲。他写的很多文章都适合非专业人士阅读。
后来,我读到他的一本书,名为《作为反叛者的科学家》(The Scientist as Rebel),书名颇具深意。由此,我想到,我们是否也应该有一本书,名为《作为反叛者的历史学家》(The Historian as Rebel)呢?
这涉及到历史学的本质:我们为何研究历史?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谁?
历史学家的使命,归根结底并非传承文化,或保存某种古代遗产。其本质在于质疑现有的历史论述,反抗并抵制种种主流的历史理解。
我们身边充斥着对历史的滥用和错用,即便历史学家自身也难以避免。可以说,我们讨论、使用并宣称的历史,多半都是靠不住的,经不起深入追究。
在我的研究领域——魏晋南北朝史和北方民族史中,同样存在许多经不起追问的常见说法。
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的开发,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改变了南方人口和经济的占比,进而影响了整个历史走向。关于其原因,中学教科书和大学课堂常给出简单解释:北方战乱导致大量农民南迁,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从而促进了南方的开发。
我学生时代曾轻易接受这一说法,甚至在成为教师后也可能在课堂上讲授过。然而,这一说法经不起追问:所谓的“先进的北方生产技术”究竟指什么?是作物品种、生产工具、种植技术,还是劳动者的组织方式?当时北方旱作农业的技术真的比南方稻作农业更先进吗?旱作农业的技术能否直接移植到稻作农业中?
这一简单说法掩盖了许多深刻的历史议题。换个角度思考,我们首先要问的是:那时的南方劳动者究竟来自哪里?他们都是北方逃难南下的流民吗?还是以土著为主?土著又是谁?除了原有的国家编户,大量不说汉语、不服属国家管理的山区土著人群(如蛮人、山越)是如何进入国家体制的?

今日所谓的南方人,他们的祖先并非都是北方移民,或主要不是。更多的是南方土著人民,他们被北方来的统治者成功改造,从蛮人、越人转变为国家体制下的新型劳动者,转变了文化和政治认同,成为了说汉语、服属王朝的华夏臣民,也就是我们今天汉人的祖先的一部分。
这一转变完成了一个深刻的历史过程:华南变成了华夏(即后来的汉人)的家园。然而,这一转变并非简单流畅或理所当然的,它充满了征服、反抗、血泪和压迫,充满了人类历史上许多已知情形下的人群对人群、体制对个体、强力对弱者所制造的痛苦。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叙述中,这些痛苦早已被掩盖、遗忘和转化,成为了一曲充满浪漫气息的、值得后人讴歌的英雄主义江南开发史。
历史叙述多半如此。即便是看起来确切无疑的说法,也经不起追问和深入推敲。
那么,历史学家究竟该做什么呢?他们应该作为反叛者、起义者、异议者,去重新考察这些历史,质疑那些被广泛接受的说法,一再地质疑。
其实,不仅历史学如此,各个学科的朋友都应如此。rebel(反叛者)这个定位对大家都适用。各个学科要做的都是重新质疑已有的说法,成为已有说法的异议者和主流的抵抗者,这不限于特定的时代、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
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时代,所有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都应该是反叛者、抵抗者。
最近,我在思考另一个话题:历史学对历史的责任问题。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不仅仅是黑暗时代的受害者,也是黑暗时代的制造者。他们参与了历史的内在发展,或至少是做了很多推波助澜的事。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纳粹德国的历史。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反犹主义从何而来?其中作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历史观,不能不说是17、18世纪以来德国历史学家的制造品。他们宣讲的民族史,特别是日耳曼民族史观,就是德奥历史学家的重要成绩。
对于日耳曼民族主义的一路上扬,这些历史学家做了大量推波助澜的工作,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是主要的责任人。后来纳粹精神的很大一部分营养即来自这里。
看看我们今天,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状况,大家各有体察。我们做北方民族史的,在网络上无论说点什么都会有人来骂。
其实我理解这些骂人的人,因为他们已经被教育成这个样子。他们骂是因为你说的历史和他们知道的历史不一样,而他们相信自己知道的历史才是真实的历史,你说的历史是错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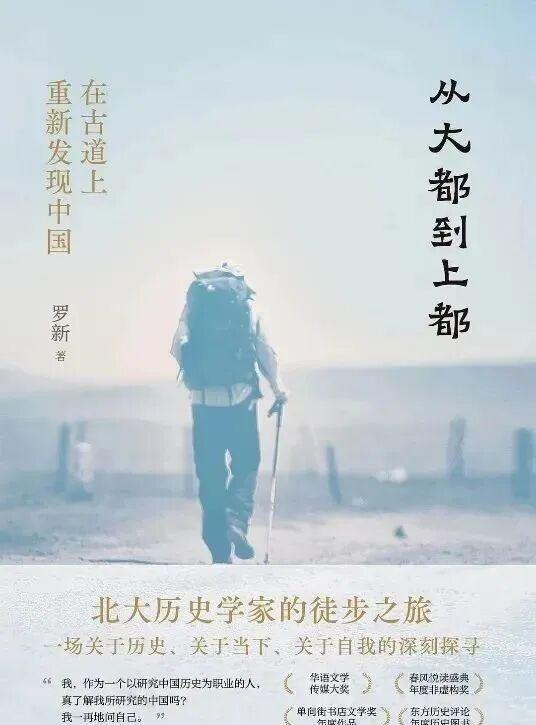
那么,他们的历史自信是从哪儿来的呢?
其实也源自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历史学自己发展出来的教条、观念或常识。这不是突然出现的,不是这几年才有的,而是很久以来、许多历史学家参与制造的。
当我们反感、反对乃至痛恨此刻正在发生着的历史时,不要忘记这个时代是慢慢形成的,不是一两天突然冒出来的。
纳粹德国不是希特勒凭一己之力突然制造出来的。希特勒式的领导人也是被历史制造的,历史知识恰恰是制造他们的原料之一。
历史学和其他一切学科大概都是一样的,都是要对各自时代的历史负责任的。这个责任我们过去检讨得不够,我们太喜欢把自己当作受害人,把责任推出去。
1945年之后,西方学界对纳粹时期的历史学、考古学有很多批判、反思。其实还应该追到更深更远的地方,因为20世纪的学者又是继承他们前几代的学者而来的。
历史学家做什么,为谁做?所谓探究真理、探究真相,该探究什么,为谁、为什么探究?这些都是应该反思的。没有哪一个学科、哪一个人能宣称自己真正掌握了真理,这是到了今天我们应该完全明白的事情。但是做什么、不做什么,做到哪个程度,这确实需要我们反思学术史上、历史上的教训。

最后,我想说四个字:“有所不为”。
今天我们必须知道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坚决不做。作为一个反叛者,有所不为是一条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