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实商业的戏剧性远超影视剧本——刚宣布辞职的宗馥莉,近期以强势姿态重返娃哈哈集团核心决策层。此次回归不仅携带心腹严学峰(此前因调查风波暂离核心岗位)共同返场,更通过宏胜饮料集团向全国经销商发出2026年续约通知,要求缴纳保证金以维持娃哈哈品牌代理权。这一动作标志着其主导的“娃小宗”项目在诞生41天后即告夭折,转而重新聚焦娃哈哈主品牌运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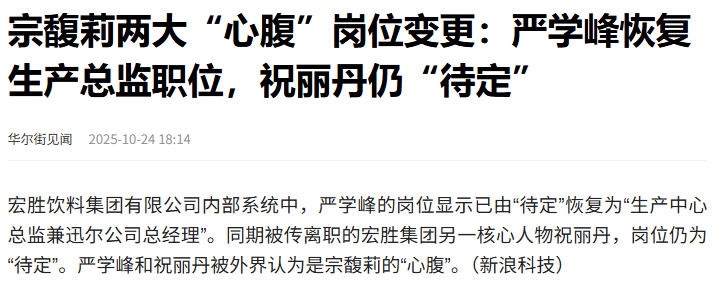
回溯2024年,宗馥莉曾以“辞职”为筹码上演以退为进戏码,迫使集团在七日内重新授予其董事长职位,并顺势清理杜建英系体外公司。此次二度回归却呈现截然不同的博弈格局:其一,去年属被动召回,今年则因“娃小宗”项目触发经销商二选一机制(代理新品牌即丧失娃哈哈资格),导致生产端与渠道端严重割裂,迫使其回归主航道;其二,身份从董事长降格为宏胜系总裁,业务主导权受限;其三,此次妥协实为品牌方与生产方的利益再平衡——娃哈哈896亿品牌价值(据世界品牌实验室2024年评估)与50亿年利润的悬殊对比,凸显“商标”与“产能”的共生依赖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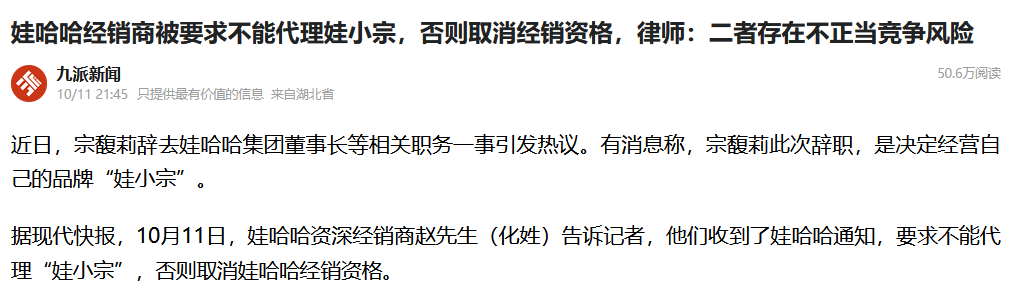
深层矛盾直指娃哈哈股权架构的历史遗留问题:杭州上城文旅持股46%为第一大股东,宗馥莉继承29.4%股权,职工持股会24.6%股权因老宗去世后回购协议争议陷入司法程序。即便宗馥莉最终掌控54%股权,仍需三分之二股东同意方可处置商标这类核心资产。当前僵局折射出中国初代民营企业的普遍困境——创始人通过体外公司体系平衡多方利益时埋下的权属隐患,在代际交接时集中爆发。

2025年上半年的股权转让谈判暗流涌动:国资方因价格分歧未与宗馥莉达成协议,杜建英系虽获18亿美元信托资金筹措意向,但受制于诉讼进程尚未启动收购。这场涉及896亿品牌资产、数万员工生计与民族商业记忆的博弈,亟需超越短期利益的结构性解决方案。毕竟,持续的内耗不仅消耗企业竞争力,更可能让承载几代人情感记忆的国民品牌沦为资本游戏的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