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焦One(dingjiaoone)原创
作者 | 陈丹
编辑 | 魏佳
曾被调侃“年年喊破圈,次次无水花”的中文播客,在2025年迎来关键转折。理想汽车CEO李想在罗永浩视频播客中落泪、鲁豫“收养”窦文涛等片段席卷社交媒体,从微博热搜到短视频平台二次创作,播客这一“小众自留地”首次闯入大众视野。
9月24日,360董事长周鸿祎做客罗永浩播客对谈AI,再次引发行业热议。这些名嘴+明星嘉宾的组合,让人看到中文播客对标国际头部节目的可能——美国“播客之王”Joe Rogan的同名节目访谈特朗普、马斯克等顶流,YouTube订阅数突破2000万,影响力远超传统播客范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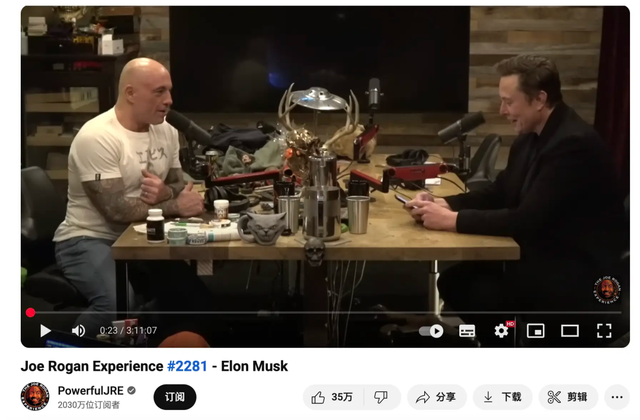
Joe Rogan节目截图
除罗永浩外,于谦、李诞、杨迪等名嘴在B站开设视频播客,单期播放量轻松破百万。互联网巨头也加速布局:小红书打造“随时随地视频播客”标签,抖音在精选板块开辟流量入口。当大厂带着流量入场,明星带着话题加盟,播客从“音频赛道分支”跃升为“内容新宠”,甚至被视为“下一个风口”。
但热闹表象下暗藏隐忧。“这会不会是虚假繁荣?”某播客主播的质疑引发共鸣。当前视频播客热度高度依赖名人效应——破圈的是李想的眼泪、鲁豫的段子,传播的是娱乐化碎片内容,与播客追求的“深度、陪伴、信息增量”背道而驰。
更关键的是,这场由名人与大厂催生的热度能持续多久?当名人新鲜感消退、平台流量转向,视频播客是否会昙花一现?中小播客主能否分到红利?这些问题至今无解。
“要不要做视频播客?”这道选择题困扰着众多播客主。小宇宙主播《置顶废话》订阅用户刚破1200人,虽登上平台热门榜单,但面对视频化仍犹豫:“谁会花时间看两个普通人聊天?”头部主播刘飞运营的《三五环》《半拿铁》订阅超80万,听友劝其“架个镜头”,他却认为当前未找到合适形式。

图源 / pexels
在刘飞看来,视频播客是“生造概念”——鲁豫、罗永浩的节目本质是访谈综艺;小Lin说、巫师财经的作品无需画面,纯听也能获取信息。所谓“视频播客”,不过是给传统内容套新壳,未形成独特形态。
这种疑虑延伸至供需两端。从供给看,视频化涉及机位、剪辑、打光等全新挑战,制作成本远超音频。中小播客主面对专业视频团队竞争,若仅将音频转视频,慢节奏、低信息量的“粗糙成品”在中长视频赛道难有竞争力。
从需求看,播客的核心优势是适配通勤、健身等“眼睛被占据”的场景。用户有时间看视频时,往往会选择信息密度更高、视听更刺激的内容,视频播客反而成为末位选项。
但行业态度两极分化。从业5年的广播人直言“声音是边缘媒体”,建议播客主重视视频化;狂喜播客节创始人关雅荻认为视频播客是趋势,制作门槛低于想象,“有话要说比技术更重要”;播客公社创始人老袁鼓励新人尝试,认为只要支持“闭屏收听”就具备播客属性。
互联网平台布局播客的核心目标是拓展增量,但B站、小红书、抖音打法各异。B站暑期投入10亿级流量,提供免费录制场地,计划上线AI创作工具,看似诚意十足,实则延续“长视频逻辑”——早期想借视频播客拓展生态,现阶段重心转向“明星大咖节目”,以低成本撬动高价值资源。
小红书走社区运营路线,推出“随时随地视频播客”话题,8-9月参与创作的用户可获5万-30万曝光资源。市场传言原小宇宙核心团队加盟小红书,足见其对播客业务的重视。但15-20分钟的内容时长与用户“碎片化浏览”习惯、播客深度陪伴属性存在矛盾。
抖音在“抖音精选”推出《奇遇记播客》,6月中旬上线至今更新28期,嘉宾均为数百万粉丝级大V。老袁认为,抖音更注重商业化效率,当前播客行业招商、付费模式不成熟,因此仅为试水,暂不会押宝。

图源 / pexels
尽管平台投入力度大,但多数播客主迁移意愿低。首先,小宇宙等音频平台已培养用户“闭屏收听”习惯,B站、小红书以视频或图文场景为主,用户想听播客仍会优先选择音频平台。其次,播客内容逻辑与平台算法错位——做播客无需适应算法规则,只需提供稳定预期,而依赖算法的平台难以滋养深度内容。
更关键的是,平台未解决商业化难题。中腰部创作者难以触达商业化资源,只有形成“创作者变现-平台吸引创作者-用户获得优质内容”的健康循环,才能稳定市场。当前热度或只是“一波流”。
播客商业化主要依赖广告和用户订阅,但两者均难以支撑行业整体发展。Statista统计显示,2024年中国播客广告总收入仅33亿元,远低于短视频平台。老袁透露,当前广告市场“买方主导”——定期投放的品牌集中在消费电子、生活服务等领域,需求有限;广告合作缺乏定价体系,品牌方通过数据监测筛选节目,但投放金额、合作形式完全由品牌决定,播客主议价权低。
此前有媒体报道,某订阅数近50万的播客,2024年3月到11月总收入19万,扣除开销后净收入仅13万。相较于广告的不稳定,用户订阅被视为更可持续的变现方式,但整个行业能依靠订阅收入稳定生存的节目不足5%。
播客商业化困境源于两大症结:一是“内容看不见”导致的效果追踪难题——广告植入多为“口播提及”,用户是否完整听到广告、是否产生消费意愿无法精准量化,让广告主持谨慎态度;二是“流量掣肘”引发的用户规模与变现效率瓶颈——2025年中文播客听众规模预计突破1.5亿人,但与抖音、B站相比仍有限,视频播客虽被视为风口,但国内用户对慢节奏、重对话的内容接受度有限,用户规模扩大与商业化突破仍存疑。

图源 / pexels
对于发展十余年的播客行业来说,商业化仍是痛点。刘飞认为,当前平台入局虽能让更多人知道播客,但能否培育深度内容用户存疑。美国用户对“talkshow”接受度高,转向YouTube播客视频顺理成章;而国内市场,即便像《圆桌派》《十三邀》这类优质对谈节目,也始终属于小众需求。
老袁比刘飞更乐观,他相信播客商业化时代终会到来。当播客成为人人可参与的社交媒体,行业生态成熟后,商业化自然会水到渠成。但在那之前,播客对大多数创作者而言,只能是自我表达的出口,而非赚钱的工具。
“它不是风口,可能也不会有大爆款,哪怕偶尔有一期数据还不错,但除了心理上的安慰外,并不会带来实际的商业回报。”老袁提醒播客主做好心理准备。肉松和室友仍在坚持更新播客,但随着两人其他工作的增加,未来能否保持更新节奏,她也没法保证。
*题图来源于pexels。
